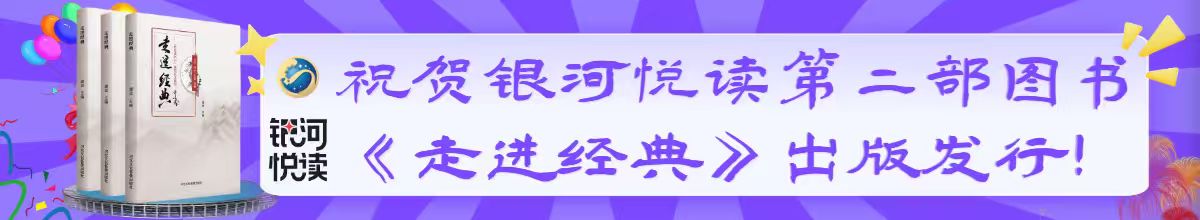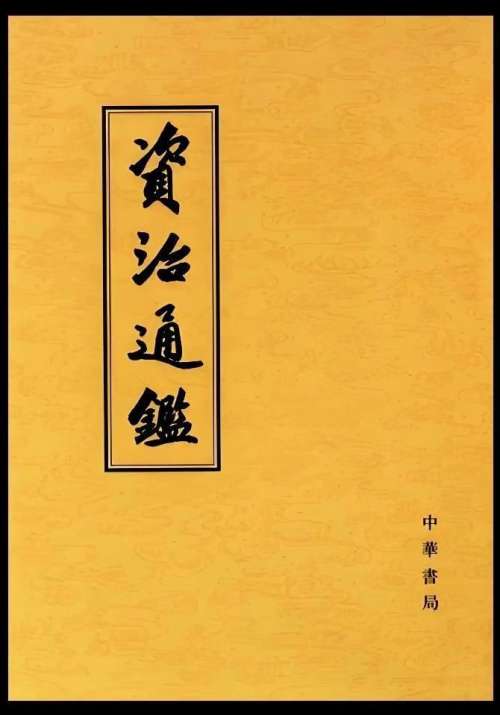
汉昭帝刘弗陵是个短命的皇帝,公元前74年驾崩,年仅二十一岁。《资治通鉴》卷二十四记载了这一重大事件,让我们看到汉朝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逻辑。原文如下:
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
春,二月,诏减口赋钱什三。
夏,四月,癸来,帝崩于未央宫;无嗣。时武帝子独有广陵王胥,大将军光与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内不自安。朗有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嗣。”言合光意。光以其书示丞相敞等,擢郎为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后诏,遣行大鸿胪事少府乐成、宗正德、光禄大夫吉、中郎将利汉,迎昌邑王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光又白皇后,徒右将军安世为车骑将军。
贺,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谏曰:“大王不好书术而乐逸游,冯式撙街,驰骋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于棰辔,身劳虖车舆,朝则冒雾露,昼则被尘埃,夏则为大暑之所暴炙,冬则为风寒之所匽薄,数以耎脆之玉体犯勤劳之烦毒,非所以全寿命之宗也,又非所以进仁义之隆也。夫广厦之下,细旃之上,明师居前,勤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其乐岂街橛之间哉!休则俛仰屈伸以利形,进退步趋以实下,吸新吐故以练臧,专意积精以适神,于以养生,岂不长哉!大王诚留意如此,则心有尧、舜之志,体有乔、松之寿,美声广誉,登而上闻,则福禄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圣,至今思慕未怠,于宫馆、囿池、戈猎之乐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圣意。诸侯骨肉,莫亲大王,大王于属则子也,于位则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责加焉。恩爱行义,纤介有不具者,于以上闻,非飨国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无惰,中尉其忠,数辅吾过。”使谒者千秋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后复放纵自若。
郎中令山阳龚遂,忠厚刚毅,有大节,内谏争于王,外责傅相,引经义,陈祸福,至于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过。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愧人!”王尝久与驺奴、宰人游戏饮食,赏赐无度,遂入见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愿赐清闲,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胶西王所以为无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闻胶西王有谀臣侯得,王所为似于桀、纣也,得以为尧、舜也。王说其谄谀,常与寝处,唯得所言,以至于是。今大王亲近群小,渐渍邪恶所习,存亡之机,不可不慎也!臣请选郎通经有行义者与王起成,坐则诵《诗》、《书》,立则习礼容,宜有益。”王许之。遂乃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王。居数日,王皆逐去安等。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
春季,二月,汉昭帝颁布诏书,将百姓的口赋(人头税)减免十分之三。
夏季,四月癸未日,汉昭帝在未央宫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当时汉武帝的儿子中只有广陵王刘胥还在世,大将军霍光与群臣商议拥立皇位继承人,众人都主张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因行为不合礼法,早已被汉武帝弃用,霍光内心对此感到不安。
有一位郎官(宫廷侍卫官)上书说:“周太王舍弃长子太伯,立幼子王季;周文王舍弃长子伯邑考,立次子周武王。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即使废黜长子、拥立幼子也是可以的。广陵王不能继承皇位。”这番话正合霍光心意,他将奏书拿给丞相杨敞等人看,并提拔这位郎官为九江太守。
当天,霍光秉承皇后(汉昭帝皇后上官氏)的诏令,派遣代理大鸿胪事务的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迎接昌邑王刘贺。刘贺乘坐七辆驿车(汉代传递公文或接送官员的专用车辆)前往长安的官邸。霍光又奏请皇后,将右将军张安世调任为车骑将军。
刘贺是昌邑哀王刘髆的儿子,在封国时一向狂妄放纵,行为毫无节制。汉武帝去世时,全国服丧期间,他仍游猎不止。曾在方与县游玩,不到半天就骑马奔驰二百里。
中尉王吉劝谏:琅邪人王吉当时担任昌邑国中尉,上书劝谏说:“大王不喜欢读书治学,却喜好安逸游乐,手靠车轼、身探车外,骑马驰骋不停。口中因呼喊口令而疲倦,手上因握马鞭、缰绳而酸痛,身体因车马颠簸而劳累。早晨冒着雾露,白天顶着尘土,夏天被酷暑暴晒,冬天被寒风侵袭。多次以脆弱的身体承受这些劳累与困苦,这既不是保全性命的根本,也不是弘扬仁义的做法。
若能在高大的房屋下、细软的毡垫上,让贤明的老师在面前教导,勤奋的学生在身后诵读,上论唐尧、虞舜的盛世,下谈商、周的兴隆,考察仁圣君主的风范,学习治国理政的方法,发奋努力到忘记吃饭,使品德日日更新,这种快乐哪里是骑马奔驰所能比的!休息时,通过弯腰、抬头、伸展、弯曲来活动身体,通过慢走、快步来锻炼下肢,通过呼吸新鲜空气、排出浊气来调养内脏,通过专心致志、积聚精神来怡养心神,这样养生,怎能不长寿!
大王若真能留意这些,就会有尧、舜那样的志向,有赤松子、王子乔那样的长寿,美好的名声和广泛的赞誉传到朝廷,福禄就会降临,国家也能安定。如今皇帝仁圣,至今仍对武帝思念不已,从未去宫馆、园林、池塘游玩,也未享受狩猎的乐趣,大王应日夜想着如何顺应皇帝的心意。在诸侯中,与皇帝最亲的莫过于大王,您对皇帝而言,论亲属是子辈,论地位是臣子,一人承担两种责任。若在恩爱、品行上有丝毫欠缺,被朝廷得知,并非保全封国的福气。”
刘贺于是下令说:“我行事难免懈怠,中尉忠心耿耿,多次纠正我的过错。”派谒者(侍从官)千秋赏赐中尉五百斤牛肉、五石酒、五束干肉。但此后,他依然放纵如故。
郎中令龚遂劝谏说,山阳人龚遂担任昌邑国郎中令,为人忠厚刚毅,有大节。他对内直言劝谏刘贺,对外指责刘贺的师傅、国相,引用儒家经义,陈述祸福得失,常常痛哭流涕,忠诚恳切不止,还当面指责刘贺的过错。刘贺甚至捂住耳朵起身就走,说:“郎中令真会让人羞愧!”
刘贺曾长时间与马夫、厨师一起游戏、吃喝,赏赐毫无节制。龚遂入宫进见,哭着用膝盖跪地前行,左右侍从也都跟着落泪。刘贺问:“郎中令为何哭泣?”龚遂说:“我为国家将危而痛心!希望大王赐我单独谈话的机会,让我尽吐愚见!”刘贺屏退左右侍从。
龚遂问:“大王知道胶西王刘端因无道而灭亡的原因吗?”刘贺说:“不知道。”龚遂说:“我听说胶西王有个谄媚的臣子叫侯得,胶西王的行为像夏桀、商纣,侯得却称他像尧、舜。胶西王喜欢他的谄媚,常与他同睡同起,只听侯得的话,最终导致灭亡。如今大王亲近小人,逐渐沾染邪恶的习惯,存亡的关键,不能不谨慎啊!我请求挑选通晓经书、品行端正的郎官与大王一同起居,坐下时诵读《诗经》《尚书》,站立时练习礼仪举止,这样应该会有好处。”
刘贺同意了。龚遂便挑选郎中张安等十人侍奉他,但只过了几天,刘贺就把张安等人全赶走了。
由于汉昭帝英年早逝,就出现了皇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按照逻辑,汉代皇位继承虽遵循“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宗法传统,但更注重继承人是否“合宜”(即是否具备治国能力、品行是否端正)。霍光等大臣否定广陵王、选择昌邑王,以及后来废昌邑王,均以“能否承继宗嗣、安定社稷”为核心标准,而非单纯拘泥于长幼顺序,体现了“社稷为重、君为轻”的政治现实。
这段文字告诉人们,君主“德”与“能”的重要性。文中通过王吉、龚遂的劝谏,反复强调君主需具备“仁圣”之德(如节制享乐、顺应民心)和“治国”之能(如读书治学、学习仁圣之道)。刘贺的“狂纵无节”(服丧期间游猎、亲近小人、赏赐无度),正是其后来被废的关键伏笔,说明汉代对君主的个人品行和治国素养有明确的期待,失德失能者难以维系统治。
我们还看到,直臣的劝谏价值与困境。王吉、龚遂作为臣子,分别以“温和上书”和“当面直谏”的方式劝谏刘贺,前者引经据典谈养生与治国的关系,后者胶西王亡国以历史教训,警示风险,体现了儒家“以道事君”的政治理想。但刘贺“放纵自若”“赶走贤臣”的反应,也揭示了古代直臣劝谏的困境——君主若缺乏自省意识,臣子的忠诚与智慧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可能引发冲突。由此可以看出, “近贤臣、远小人”的治国警示。龚遂以胶西王因亲信谄媚之臣侯得而亡国为例,指出君主“亲近群小”会导致“渐渍邪恶”,危及社稷。这一观点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强调君主的身边人,如侍从、近臣对其行为和决策的影响,警示统治者需谨慎择友、远离奸佞,才能保全自身与国家。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