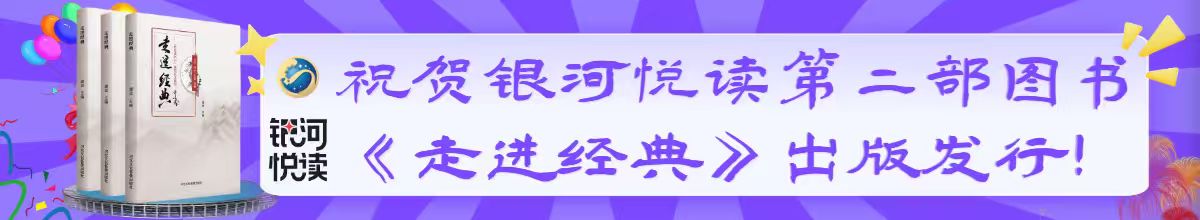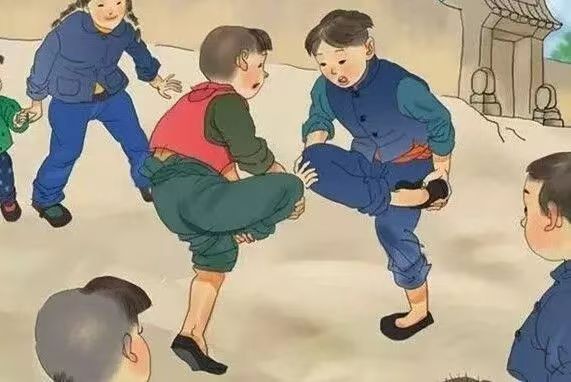
60后的人说:“我的童年在田野里”。
70后的人说:“我的童年在街巷里”。
80后的人说:“我的童年在书本里”。
90后的人说:“我的童年在电视机里”。
00后的人说:“我的童年在电脑里,在手机里,在网游里……”。
我们都有自己的童年,玩是童年时代的主题。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的童玩是在沧浪河畔的花园垛田埂间、南城门外街巷里、舒家巷冷家大院内、东方红小学操场上度过的。“炸地雷、玩弹弓、滚铁环、躲蒙子、粘知了、弹玻璃球、抽蒋秃头、打水漂、斗公鸡、挤暖和……”我和小伙伴们在玩中接受挑战、承受挫折、理解友爱、学会等待、懂得分享,在无忧无虑地玩耍中幸福快乐地成长。
那时候,偶尔得到一挂小鞭炮,我和小伙伴总能玩得花样百出。用一只口盅扣着鞭炮,随着噼噼啪啪的闷响,口盅像一只蛤蟆一样跳来跳去。索性把鞭炮拆散,一枚一枚点燃引线,待它快烧完时扔进水里,噗的一声,水面浮起一缕白烟,像一朵白花突然从水下冒出来。最好玩的是“炸地雷”。先把泥土浇点水,使坏的吐痰或尿水,就变成稀泥,再做成烧饼圆型,我们称“响雷吧吧”。把鞭炮插在路中间的“响雷吧吧”上,看到有人过来时把它点燃,躲闪一旁,“敌人”越走越近,砰地一声,“响雷吧吧”被炸得天女散花。顿时觉得自己成了用“地雷战”伏击日本鬼子的平原游击队,中了埋伏的大人追赶逃跑的我们,破口大骂:“哪家的没教养,捉住打断你的腿!”
最便于携带,随处可玩的,便是弹弓,因为遍地都可以捡得到射出去的小石子。做弹弓的材料里,最好寻的是弹弓叉了。上放学的路上,路旁小槐树林里河边柳树下仰头张望的孩子,十有八九是寻人字形树杈的孩子。因为槐和柳做的叉子,结实,韧性好。一旦发现有中意的树枝,便猴子似的噌噌爬上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折下。三个叉的枝头处砍截整齐,在前面两叉尾端刻两个凹槽,拴胶皮不滑脱。剥去树皮,用削铅笔的小刀仔细刮磨,直至净光溜滑,那认真劲儿,比做家庭作业强太多。作动力用的胶皮,一般都是从自行车用坏的里胎剪下来的。那时巷里谁家要有辆自行车,那就是现在的宝马,奔驰了,自然极珍贵。里胎上是补丁摞补丁,大多不用时,也剪不出几个好的弹弓胶皮了。当时更高级的弹弓胶,是医院里用的输液管。又轻又软,弹性好,射程远。有了弹弓,也就有了伙伴之间的各种比赛。最常见的,是在空地上摆一摞石头,站立一定的距离,轮流来打,中次数多者为胜;也比赛打鸟的,那时没有保护鸟类的意识,还把麻雀等称为四害之一,鼓励打灭。可总打不到几个的,毕竟自己做的弹弓射程近,机灵的小鸟也不好瞄。我常用弹弓打坏别人的玻璃,檐上的老瓦,被人找到了家,少不了父母的打和骂。
我上小学时,特别流行“滚铁环”。铁环是当时男孩子的炫技宝物,那时能拥有一个称心如意的铁环,是每个小伙伴梦寐以求的事。将铁环斜背于胸前,每个人俨然就是一名所向披靡的战士,一个身背乾坤圈法力无边的转世哪吒。那时我们上学不需要大人接送,吃过饭约起邻居的小伙伴,滚着铁环奔走上学,一路上铁环哗啦哗啦地响着,声势浩大,还能推出许多花样来:有时推着铁环走;有时推着它插上盘花,走8字;有时玩起高难度地动作,放上几个障碍物在它们之间,来回推动,谁的铁环先倒了,他就为输了。画上一条线,选出个裁判,喊个一二,和运动员一样,抓紧时间推动。谁最先跑到终点,谁就是第一。
舒家巷冷家大院是兴化籍民国人物、原国民党陆军中将冷欣先生留给内侄居住的,一座占地近200平方开阔的大院子,那是我们常打乒乓球的好战场。三三俩俩地将家里的洗衣板,拿来用骨牌凳搁起,便是乒乓桌了;中间也不用什么球网,而是两块瓦砖架上一根短竹竿,再于竹竿上放上一根红领巾而已;最简陋时,也会以一根拖把或扫帚柄代之,最后左右分两伙就开始“战斗”。就是这样简陋的乒乓设备,玩的孩子还挺多呐,其中热闹和快乐却丝毫不减。惟一的遗憾就是粥少僧多,为玩不上而烦恼。当时,我因为刚接触打乒乓球,就觉得非常好玩,简直是上了瘾似的,每天一放学就和一帮小伙伴围着球台打,中午就算是饿了也不回家吃饭,就一直在那打,直到老妈亲自来叫我回去吃饭才舍得回去。
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我总是匆匆忙忙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一搁,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河对面花园垛,玩野外“躲蒙子”的游戏。草垛、谷堆、树林、草屋、鸡窝、猪圈、茅坑都是理想的藏身之所。那次我藏身在一个放草料的浅坑里,上面还盖了一层薄薄的稻草。我仰面躺着,呼吸着过夏的稻草甘香的气息,可以毫不费劲地看到头顶密集的星星。我听到寻找者的脚步声,从我身边走过去,或者徒劳地在我藏身的周围徘徊。我大气也不敢出,心里怀着秘密不被揭穿的喜悦。不一会儿,被找出来走到中间空地上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找到,我是这场游戏中最后的胜利者。我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开始还咋咋呼呼的,后来就带着点哭腔了,他们找遍了一个个可能藏人的地方。就在我暗自得意的时候,心里突然一阵紧缩,我这是在哪里呀?我突然非常强烈地感到我被这个世界遗忘了,我是在一个醒不过来的大梦里——我把自己弄丢了。小伙伴们的脚步渐渐远去,我为自己那一刻的处境感到惊骇,感到了针刺般的疼痛和恐惧……此时,不远处传来一阵熟悉而急促的呼喊声,是爸爸,那是爸爸在喊我的名字。那声音,不豪壮,不悠扬,却充满希望和力量,那是我生命里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此刻,我不再害怕和怯弱,而是像男子汉一样勇敢地爬出浅坑。
那年头,同龄的小伙伴玩得最多的游戏——“打仗”。那时候,我们上小学时的功课其实不紧,但最不想干的事是考试,最喜欢干的事却是打仗。在放学的路上敌我双方就相约好了,选择在学校对面花园垛战场开战。我们把书包堆在田埂上,“解放军”主要标识便是用杨柳枝编成一个圈,戴在头上;或从门联上撕下两块已不太红的红纸,粘在领子上。充当“敌军”的肯定鼻涕眼泪要多点的孩子,平时公认会“捣蛋”些的。我们分了谁是司令、军长、师长、旅长……人人都有官当。谁都得听从司令的。有一次,看了小画书《四渡赤水》后,我突发奇想:先奔赴学校大门口,跨过忠东桥,一渡沧浪河,到对面的花园垛田庄绕道;再跨过忠东桥,二渡沧浪河,穿插南大街;又跨忠东桥,三渡沧浪河,穿过南公路;最后跨过忠东桥,挥师舒家巷西头,大迂回到对方的背后,这样达到奇袭的效果,最终我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二天大家一致推举我做司令。自然这“司令”也就只当了一回,以后四十年来就再也没当过那么大的官。
盛夏到了。我和伙伴们一溜烟的丢掉早已破旧的布鞋,了无束缚,光着脚丫,满地乱跑。也该是蝉鸣的季节吧,午后,顶着似火的骄阳,我们溜进沧浪河对面花园垛,钻入密不透风的树林,从众多的蝉音中分辨出目标,悄悄地猫着腰屏住呼吸接近,小心翼翼地把竹竿伸到目标的背后,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一抖,蝉就被牢牢地粘住了。蝉挣扎几下,发出几声凄厉的叫声后乖乖就范。有一次,我和同伴小强一个下午都在捉蝉,那天大概手气特好,斩获颇多,于是兴致勃勃乐而忘返。不知不觉已到了晚饭时分,哪晓得小强的妈妈久等不得,竟手持着鸡毛掸子寻将过来,此时小强正手握长竿捕得兴起,丝毫未察觉妈妈已怒气冲冲地来到了身后,只见小强刚欲套蝉时,他妈妈的鸡毛掸已落到了他的头上,随着“啪,啪”两声,竿落蝉飞。小强不知是因为挨了打还是因好不容易套住的蝉又飞了而惋惜,“哇,哇”地边哭边跟着妈妈回家了。第二天我们就将刚学过不久的一句成语编了送他,叫:小强捕蝉,老妈在后。
一到放暑假,太阳当空照,热浪滚滚来,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最凉快的就是到沧浪河里去洗澡。穿条短裤,踏着发烫的石板路,走到河边码头上,脱了裤子,“扑通”一下,跳进清澈的沧浪河里。在清凉的河水里洗一会,身上爽极了,紧接着大伙就上岸玩起打水漂的游戏。打水漂游戏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真正要玩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我属于那种不太会打水漂的,超常发挥时最多三连漂。笨鸟先飞。我决定向同学中的高手小强讨教怎么才能打得好,打得远。我花费攒了几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小人书,“贿赂”小强,让他手把手地现场教我打水漂。到了河边,小强找来了一块薄石片,弯着腰,胳膊向右甩了一下,“嗖”地扔了出去。石片在水面上跳着“芭蕾舞”,又仿佛“蜻蜓点水”漂得很远很远,是那么轻快敏捷。我原以为石片会扎进水里,可石片却贴着水面腾空而起,跳跃了一下、两下、三下……哇,好神奇,没有腿的石片在水面上居然跳了十四次。“打水漂,石片要尽量薄,扔的时候角度要平,动作要快,不能使猛劲,得用巧劲。”这是小强的秘诀。于是,我找了一块很薄的石片,选好角度,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扔了出去。哈,石片没有辜负我的希望,贴着水面跳了起来,动作是那么轻盈,以至于水面只漾起一点波纹而且只一瞬间。一下、两下,居然跳了五下。我的水漂打得可厉害了,最多的时候它能连续击出十几次,最后才踉跄一下,沉人河底,激起几丝微澜。
只要有时间,上课前和放学后,我们就会玩玻璃球,甚至课间十分钟,三五成群地凑在一起,拿出自己的琉璃球摆开战场。我们撅着屁股趴在地上,或作举手射击姿势,或作丈量神态,全神贯注,那份投入,那份专注,比听那无聊的语文课要认真得多。弹玻璃球有点像现在的打保龄球,谁的玻璃球先弹进洞里就算谁赢。伙伴们很在乎自己的输赢,谁都不愿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拱手送给别人,因此游戏玩得相当激烈,什么球动了,人站的不是地方了,撞没撞到球了,不符合规则了等情况总会引起一阵争吵来,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这个时候总会有一个稍大的孩子来主持公道,一场激战告一段落,游戏继续进行,不过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了。直到有谁的母亲扯着大嗓门喊:“你个欠收拾的,看看天都黑了,还不赶紧回家馕饭!”孩子们赶紧抓起自己的琉璃球散了。胜利者衣兜里揣着胜利品满脸惬意叮叮当当地回家了,那输了玻璃球的小伙伴虽然兜里少了几粒琉璃球,但也是一脸的不服气,一边往家里走着一边不甘心地嚷着:“明天接着来啊,看我早晚得把你贏光!”
兴化方言称陀螺为“蒋秃头”。下课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去操场抽“蒋秃头”。这个时候往往是最热闹的,只见操场上,男同学们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各自喊着自己的“蒋秃头”,互相碰仗。操场的上空,便喧腾着阵阵热浪,弥漫着鞭梢叫劲的“噼噼”声。那时的院子、操场便成了我们过把瘾的地方,狠狠地抽动“蒋秃头”,飞快地旋转,一如转瞬即逝的童年。抽“蒋秃头”的时候大家总是玩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面红耳赤。不管是输是赢,都在奋力争先,玩起来就是一晌半晌,直到大人们多次喊吃饭时,才恋恋不舍地“收工回家”。如果白天打得不过瘾,我们就在月光下继续战斗,感觉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
“斗公鸡”是兴化方言,有的地方叫“斗鸡”“撞拐子”。“斗”与“撞”这两个字都揭示了游戏的性质,是激烈的身体对撞活动。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膝盖部位,手提悬着的大脚,形成一个铁三角,那膝盖骨自然就是“鸡嘴”了,用手扶着,不让它松落下来,膝盖向前,威风凛凛,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有一次,课间我想出妙招,将曲起的腿用绳捆在另一腿上。我正与对手酣战,此刻上课铃响,一时无法解开死结的我,只得单腿蹦进教室。班主任金老师见我低头忙乱,就叫我上黑板做题。我单腿踉踉跄跄地冲上黑板前,很快就把那道题解决了。在全班同学们的哄笑声中,我单腿又是连蹦带跳地回到座位,胜利凯旋。金老师也不禁笑了,放弃惩罚我的念头。
到了冬天,天寒地冻。教室外,一股强劲凛冽的寒风呼呼地吹着,即使关好教室的门窗,寒风还是丝丝从门窗缝里钻进来,室外冷得要命,室内还是冷得要命。因为要安安静静地坐个一节课,那双脚啊更是插在了冰窟里似的,那滋味可真不好受。老师讲的什么,我们都无心听进去,因为我们已经冻得麻木了,脚也失去了知觉了。但,只要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就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轰地一下飞出了教室。女同学就会在教室前的场地上踢键子、跳皮筋。不知是哪个男同学大声地说了一句:“挤暖和去。”话音刚落,很快就有十多个同学纷纷响应。挤暖和就是一种游戏,其玩法也很简单,同学们靠墙站成一排队伍,少则四五人,多则一二十人,大家喊着口号从两侧的队伍往中间使劲地挤,两端的人往中间挤压,形成两股力量。10分钟的课间,我们一边挤一边齐声高喊:“挤,挤,挤暖和,挤掉谁,谁尿床,挤毁孩子不要娘!”被挤出中心的同学,会骤然感到寒冷,于是搓着手跺着脚,哈着寒气又迅速站到队伍的一端,继续拼命地往回挤,往里挤,设法挤到温暖的队伍里面去。在这种反反复复中,我们挤得热火朝天满头大汗,用原始而简单的方法,在寒冷的冬天里,享受自己通过运动挤出来的温暖。上课铃声突然敲响,我们一哄而散,瞬间,专注挤暖和子的同学往往因另一方力量突然撤走而扑倒在地,一个压一个,赶紧慌慌张张爬起来奔进教室。进了教室,后背是土的我们相互拍打,教室里尘土弥漫。老师进来,劈头盖脸地一顿训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乐此不疲……
玩,是孩子们的天性;玩,是童年里不可或缺的元素;玩,让孩子成为孩子。童玩,那天真无邪、快乐无限去难返的快乐时光,早已在岁月的长河、岁月隧道中消失,如今只能在记忆中搜寻、梦境中再现……
愿童心不泯,愿快乐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