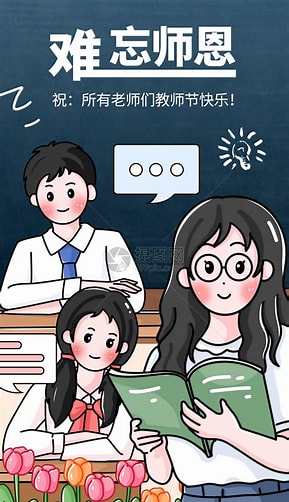
一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
书上说:西藏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在去那里游玩的旅行团中,我幸运地结识了江苏省作协成员、徐州著名作家杜长明先生。听闻我喜欢文学,想写新疆游记,杜老师的圆脸笑成弥勒佛,热情地鼓励道:小冯,不要怕,你动手写,我帮你修改。写好发给杜老师,没多久收到他的回信:写得不错,我推荐给月映轩窗公众号吧。文章发表,居然有不少点赞的,我兴奋地夜不能寐。于是,经常收到杜老师的微信:小冯,你要多写啊,我帮你改。《我家的菜园》,他帮助改成《童年的菜园》,推荐发表在《文化丰县》杂志上。看到变成铅字的、自己的文章,我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呐喊:我要写更多的作品!说句脸上贴金的话,杜老师看我是可塑之才,还有意无意地介绍我认识作协的前辈。一年半后,我叩开了徐州市作协的大门。
二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捧起一簇浪花,你却给了我整个海洋。”
初次和徐州市作协顾问李继玲老师见面,她竟然称呼我:“冯老师”。我内心膨胀,不甘放弃机会,在分手的那一刻,壮着胆子问:”李老师,我是一个文学小白,偏爱地方史,想用手中的笔,记录徐州地方的变迁,苦于没有实力,该怎么办好?”李老师停下脚步,站在街道的拐脚,眉毛稍稍一抬,眼睛柔和地笑着:“冯老师,你可以先阅读自己喜欢的名家作品,仔细揣摩,然后模仿。另外,尝试着多写,慢慢有了积累,再考虑形成自己的风格。”“还有,你没有能力写鸿篇巨作,就一个地方、一件事地写,集腋成裘,落笔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徐州的变迁史。”最后,她一脸真诚地说:“冯老师,你的作品我拜读了,已经具备了市作协成员的写作水平,你可以的。”我心中狂喜,道声谢谢,告辞走人。一丝凉风吹来,忽然想起:李老师陪着我,在闷热和蚊虫叮咬的街角,站了近一个小时,已过花甲之年的李老师啊!依照李老师传授的锦囊妙计,我先后完成《远去的大菜屋》、《赶庙会》、《我家曾住余窑北》。最后一篇,李老师看过,很是欣赏,立即推荐发表在《徐州日报》上,引起一片点赞。至此,我写家乡的底气更足了。
三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撷取一枚红叶,你却给了我整个枫林。”
我的几位老师,或温润如玉、或谦谦君子,唯有朱安华老师遵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为师之道,如鞭、似烛,时时鞭打我,刻刻照亮我,使我不敢懈怠。有感文学素养的不足,我报名跟朱老师学习写作技巧。朱老师本是电视台栏目负责人,却偏偏喜欢三尺讲台,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即给三家大学做客座讲师。一口气干了三十年,如今依旧发挥余热,奋斗在教学的前沿,这回不教青年大学生,转教老年大学的学生。朱老师丰富的知识、全面的文学素养经常赢得满堂喝彩。有时候,我私下想:朱老老师为什么有那么丰富的知识积累?时间偏爱他吗?有时候,我在课堂上小声说话,说时迟那时快,两道锋锐的目光,马上像探照灯一样扫射过来,吓得我立刻正襟危坐;有时候,我想偷懒,他张嘴即来,用春秋笔法、指桑训槐,教导我一番;有时候………朱老师,你不是春天、不是海洋,您是枫林!虽然历经紫外线的磨砺,面部有些微黑,但是,不耽误您在所有学生心目中——光彩夺目。
四
“让我怎样感谢你,当我走向你的时候,我原想亲吻一朵雪花,你却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两千年前,西方的诗歌是叙事的,唯有中国的诗歌可叙事、可言志、可抒情。中国最早的诗歌——《诗经》中的《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辞浅而义深,谁又能不着迷呢。因为喜爱古诗词,我还报名跟徐州诗词协会副主席李敏老师,学习诗词创作。李老师本是地质大队的,为了对抗大自然,长得高高大大,唯有儒雅的气质,一如诗词里的男主。他用对诗歌的热爱,和师承的吟哦技艺,给我搭建了一个银色的童话世界。听李老师吟哦是一种享受,他以独特的韵律和节奏,给同学们带来愉悦和宁静,极富感染力。他那浑厚的男中音,或高亢激越,犹如千军万马在奔腾;或轻轻呢喃,仿佛在跟风、跟云、跟流水对话,充满了灵性。
我的几位老师如此的不同,却又都诲人不倦。感谢你们,是你们给了我春天、给了我海洋、给了我枫林、给了我银色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