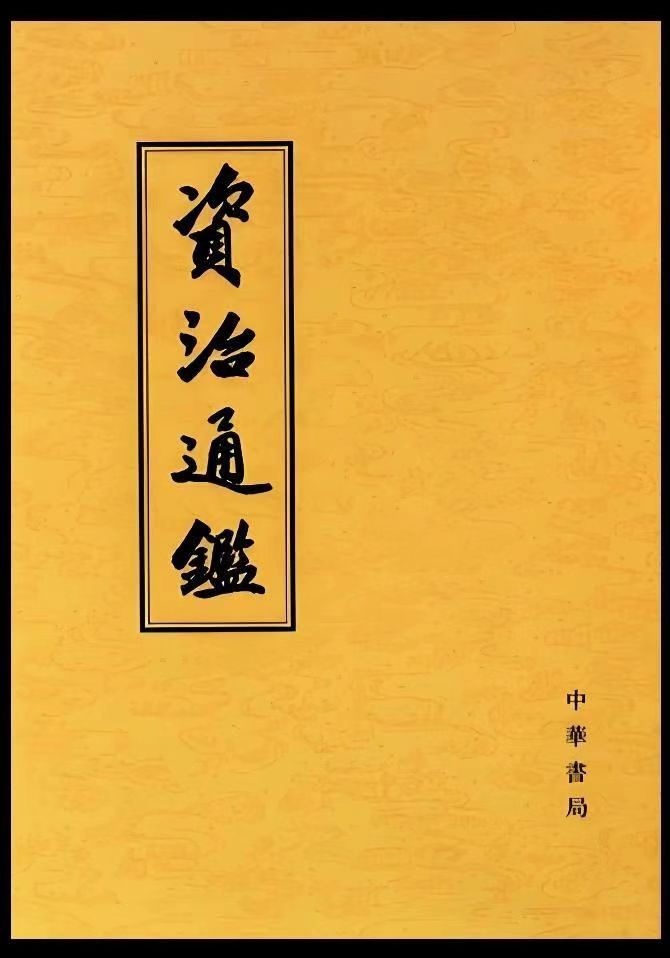
霍光长期辅政专权,成为最重要的权臣。即使在霍光去世后,他的影响依然很大。霍家的权力已经威胁到皇权,这就使得汉宣帝必须除掉霍氏家族的势力。《资治通鉴》卷二十五记载了这段历史,原文如下:
帝自在民间,闻知霍氏尊盛日久,内不能善。既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馀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后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门;御史为叩头谢,乃去。人以谓霍氏,显等始知忧。
会魏大夫为丞相,数燕见言事;平恩侯与侍中金安上等径出入省中。时霍山领尚书,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关尚书,群臣进见独往来,于是霍氏甚恶之。上颇闻霍氏毒杀许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为光禄勋,出次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为安定太守。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顷之,复徙光长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为少府。戊戌,更以张安世为卫将军,两宫卫尉、城门、北军兵属焉。以霍禹为大司马,冠小冠,亡印绶;罢其屯兵官属,特使禹官名与光俱大司马者。又收范明友度辽将军印绶,但为光禄勋;及光中女婿赵平为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将屯兵,又收平骑都尉印绶。诸领胡、越骑、羽林及两宫卫将屯兵,悉易以所亲信许、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究民犯法,奸轨不胜,于是使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浸密,律令烦苛,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廷尉史巨鹿路温舒上书曰:“臣闻齐有无知之祸而桓公以兴,晋有骊姬之难而文公用伯。近世赵王不终,诸吕作乱,而孝文为太宗。繇是观之,祸乱之作,将以开圣人也。夫继变乱之后,必有异旧之恩,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无嗣,昌邑淫乱,乃皇天所以开至圣也。臣闻《春秋》正即位、大一统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与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统,涤烦文,除民疾,以应天意。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则指导以明之;上奏畏却,则锻练而周内之。盖奏当之成,虽皋陶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何则?成练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唯陛下省法制,宽刑罚,则太平之风可兴于世。”上善其言。
我们首先来看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宣帝在民间时,就听说霍氏家族长期权势显赫,内心早已不满。等到他亲自处理朝政后,任命御史大夫魏相为给事中(加官,可出入宫廷)。霍显(霍光之妻)对霍禹、霍云、霍山(均为霍光子孙)说:“你们不努力继承大将军(霍光)的遗业,如今魏大夫担任给事中,一旦有人挑拨离间,你们还能自救吗!”后来,霍氏与魏相的家奴因争路起冲突,霍氏家奴闯入御史府,甚至想踢魏相的家门;御史(魏相下属)磕头道歉,家奴才离开。此事传到霍氏家族耳中,霍显等人这才开始感到担忧。
不久,魏相升任丞相,多次在非正式场合(燕见)向宣帝议论政事;平恩侯许广汉(宣帝外戚)与侍中金安上等人也能直接出入宫廷。当时霍山兼任尚书(掌管宫廷文书、传达诏令),宣帝却下令让官吏百姓可直接上奏密封的奏章(封事),不必经过尚书;群臣朝见皇帝也可单独往来,于是霍氏家族对此非常厌恶。宣帝隐约听说霍氏曾毒杀宣帝原配许皇后,但尚未查实,便先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平陵侯范明友调任光禄勋(掌管宫廷宿卫),将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外放为安定太守。几个月后,又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外放为蜀郡太守,将霍光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外放为武威太守。不久,再将霍光的大女婿——长乐卫尉邓广汉调任少府,掌管皇室财政。戊戌日,宣帝改任张安世为卫将军,将未央宫、长乐宫的卫尉,以及城门、北军的兵权都交给了他;任命霍禹为大司马,却让他戴小官帽(规格低于霍光旧制),且不授予印信绶带;撤销了霍禹的驻军和官属,只让他保有“大司马”的空名,与霍光当年的大司马职位名义相同却无实权。又收回了范明友的度辽将军印信绶带,只让他担任光禄勋;霍光的中女婿赵平原本任散骑、骑都尉、光禄大夫,掌管驻军,宣帝也收回了他的骑都尉印信绶带。凡是掌管胡骑、越骑、羽林军以及两宫卫尉所属驻军的官员,都被宣帝换成了自己亲信的许氏(外戚)、史氏(外戚)子弟。
当初,汉武帝在位时,频繁征调百姓服役、缴纳赋税,导致百姓贫困消耗,走投无路的百姓纷纷犯法,作乱之事层出不穷。于是汉武帝让张汤、赵禹等人逐条制定法令,出台了“见知故纵法”,也就是知道他人犯法却不举报,以纵容罪论处。“监临部主法”,监管官员对下属犯法负有连带责任。同时放宽对“故意加重刑罚”的惩处,却严厉追究“放纵罪犯、减轻刑罚”的责任。此后,奸猾的官吏们纷纷钻法律空子,互相攀比效仿严苛执法,法令的网罗越来越严密,条文也越来越繁琐苛刻,公文堆满了桌案楼阁,负责主管法令的官员都无法通读全部内容。因此,各郡国在沿用法令时出现混乱,有时罪行相同,判决却截然不同;贪官污吏趁机操纵法令谋利,想让罪犯活下来,就找“从轻量刑”的案例附会,想让罪犯被处死,就找“从重定罪”的案例比照。议论此事的人都为百姓的冤屈感到痛心。
廷尉史(廷尉下属官员)巨鹿人路温舒上书说:“臣听说,齐国发生公孙无知之乱,齐桓公才得以兴起;晋国发生骊姬之难,晋文公才得以称霸。近代赵王刘如意(刘邦之子)不得善终、吕氏家族作乱,孝文帝刘恒才得以成为太宗(庙号)。由此可见,祸乱的发生,往往是为了让圣贤君主登上历史舞台。在变乱之后继位的君主,必定会推行与过去不同的恩惠政策,这是圣贤君主彰显天命的方式。过去昭帝去世后没有子嗣,昌邑王(刘贺)因淫乱被废黜,这正是皇天为陛下(汉宣帝)这位至圣君主开辟道路啊。臣听说《春秋》重视君主即位的正统性、天下一统的原则,且注重开端的规范。陛下刚登上至尊之位,天意与人事相合,应当改正前代的过失,规范即位后的统治纲领,废除繁琐的法令条文,消除百姓的疾苦,以顺应天意。
臣听说秦朝有十大过失,其中一条至今仍在延续,那就是负责司法的官吏(滥用刑罚)。司法是天下最重要的大事:死去的人不能复活,断裂的肢体不能复原。《尚书》说:‘与其杀死无辜的人,宁可承担“不按常规执法”的责任。’如今负责司法的官吏却不是这样,上下互相驱使,把严苛当作明察,执法越严酷的人越能获得‘公正’的名声,执法平和的人反而多有后患。因此,负责司法的官吏都想让罪犯死——并非他们憎恨罪犯,而是他们保全自己的办法,就在于让罪犯被处死。于是,死人的鲜血在街市上流淌,受刑的囚犯多得肩并肩站立,被判处死刑的人,每年数以万计。这正是仁圣君主感到痛心的原因,太平盛世未能实现,全是因为这个缘故啊。
人之常情是,生活安定就乐于活下去,遭受痛苦就想一死了之。在严刑拷打之下,罪犯还有什么供词得不到呢!所以,囚犯受不了痛苦,就会编造虚假的供词;官吏们利用这一点,就会引导囚犯明确‘罪行’;上奏案情时担心被驳回,就会反复罗织罪名、歪曲事实,让罪名成立。等到判决文书完成,即使是古代善于断案的皋陶(舜时司法官)来审查,也会认为罪犯死有余辜。为什么呢?因为罗织罪名的证据太多,刻意编造的罪行太明显了。所以俗语说:‘在地上画个圈当作监狱,没人愿意走进去;用木头刻个官吏,没人愿意去对质。’这都是百姓痛恨官吏严苛的心声,是充满悲痛的言辞啊。希望陛下减省法制,放宽刑罚,这样太平之风就能在天下兴起了。”宣帝认为路温舒的话很对。
大臣的权力过大,就会威胁到皇权,甚至危害朝廷的运行。这样就产生了皇权与权臣的权力博弈。这段历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汉宣帝意识到,霍家的权力过大,威胁到皇权,于是通过“明升暗降”,比如让霍禹任大司马却无实权、外放霍氏亲信、替换兵权等手段,逐步削弱霍氏势力,本质是君主集权与权臣专权的对抗,最终目的是收回旁落的皇权,巩固统治正统性。我们看到霍氏因霍光辅政长期掌权,已威胁皇权。
这段文字还说明严刑峻法的危害与司法公正的重要性。汉武帝时期的法令繁琐严苛,导致官吏滥用职权、百姓冤屈丛生,路温舒的上书直指核心,司法是“天下之大命”,过度严苛会背离仁政、激化社会矛盾;汉宣帝认可其观点,体现了“仁政需轻刑”的治国理念,也为后来汉朝“中兴”奠定了法制基础。
这段文字还说明了一个朝代“乱后求治”的治国逻辑。路温舒提出“祸乱兴圣贤”,强调变乱之后的君主应“改旧失、施恩惠”,这一观点契合汉宣帝的处境,他在继位前经历昌邑王被废以及霍氏专权,也成为古代君主“拨乱反正”的重要治国思路,通过修正前代弊端、顺应民心,实现政权稳定与盛世。
二〇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