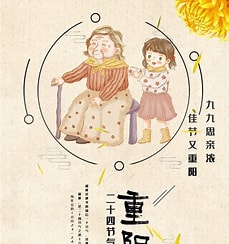
厨房的蒸笼刚掀开,重阳糕的甜润香就裹着茱萸的辛香,顺着门缝往外钻,裹着股实在的暖。妈妈系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手里捏着细麻绳,正把重阳糕切成菱形,糕面上的桂花碎落在桌布上,星星点点的。“你奶奶说,重阳糕得就着茱萸吃,能驱邪安神,这是老辈儿传下来的规矩。”她话音刚落,窗外就传来爷爷的咳嗽声,我探头一看,老爷子正摩挲着墙上挂的酸枣木拐杖 —— 那是去年登高时,他在山脚下亲手捡的,杖身磨得发亮,顶端还磕了个小缺口,是岁月磨出来的印记。
小时候在老家过重阳,可不只是敬老,最庄重的是祭祖。奶奶擦得锃亮的八仙桌上,摆着刚蒸好的麻糍,软乎乎的能拉出丝;新收的小米装在粗瓷碗里,粒粒饱满;还有奶奶亲手酿的菊花酒,装在陶坛里,酒液清亮,喝着带点菊花的清苦。她用蓝布缝了个小香囊,针脚密密的,还绣了个小小的“安” 字,把晒干的茱萸装满,往我衣襟上一挂:“给老祖宗送秋粮,也求他们保佑你平安。咱庄稼人靠天吃饭,可不能忘了报本思源。”香案前的烛火晃悠悠的,奶奶嘴唇动着,念叨着“求老祖宗保佑庄稼丰收,孩子们平安长大”,那些朴实的祈福话,我至今记着。麻糍的糯香混着纸钱的烟火气,成了我最深刻的重阳记忆。后来才知道,这重阳打战国时就是祭祖节,是丰收后谢天地祖先,也是盼来年风调雨顺。
那茱萸囊我戴到上学才舍得摘,那股辛香总让我想起爷爷讲的老话。他说,古时候重阳登高、佩茱萸,不是图乐子,是怕九月九有灾厄,茱萸是“天然防疫包”,登高是“避险大招”。我第一次登高是十岁,跟爷爷去村后的龙山。山间小路坑坑洼洼,爷爷的拐杖笃笃地敲着石板路,他走几步就喘口气,却不肯让我扶:“我还走得动!”到了山顶,风刮得茱萸囊晃悠悠的,爷爷从怀里掏出个小锡酒壶,倒出两杯菊花酒:“尝尝,你奶奶去年酿的,存了一整年才开封。”酒液清冽,辣得嗓子眼发麻,却越品越香。爷爷说这酒能“辅体延年”,还念叨着陶渊明重阳无酒,友人送酒对花痛饮的事:“文人风雅是一方面,咱老百姓登高,更想望一望家的方向。”我扶着他,看漫山野菊开得金黄,远处的村落炊烟袅袅,心里忽然就懂了。
如今在城里过重阳,仪式简了,情意却没减。妈妈还酿菊花酒,就是不再等一整年,采了新鲜菊花,混着黍米和冰糖,装在玻璃罐里泡半月就开封,酒液清甜,少了烈性,多了些生活的柔和。爸爸早早就去市场买重阳糕,特意跟老板说:“多插几面五彩小旗,俺爹娘看着高兴,糕谐音‘高’,图个福寿绵长。”
傍晚带着重阳糕和菊花酒去看老人,奶奶正坐在阳台剥茱萸,手指关节有点变形,撕得慢,却一片都不浪费,嘴里念叨着:“给重孙缝个新香囊,保他平平安安。”爷爷戴着老花镜,翻着手机里去年登高的照片,手指在屏幕上摩挲着:“今年腿脚还行,咱爷俩还能再爬一次山。”
我陪着爷爷在小区的小山坡上慢慢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他的拐杖笃笃地敲着碎石路,步子比从前慢了,走几步就停一停。风里飘着菊花香,爷爷忽然念起“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念完叹口气:“其实登高插茱萸,说到底是惦记亲人啊。”我扶着他的胳膊,能摸到他袖口磨毛的布料,心里暖乎乎的。
奶奶的祭祖是谢老祖宗,爷爷的登高是盼日子好,妈妈的菊花酒是疼长辈,爸爸的重阳糕是祈福寿。这重阳的四味情怀,从来不是割裂的仪式,是揉进秋日时光里的实在暖。晚风里,爷爷的笑声混着孩子的嬉闹,手里的重阳糕还带着温度,咬一口,软糯香甜裹着茱萸的辛香,忽然就想起小时候奶奶塞给我的茱萸囊,针脚有点扎手,却暖得踏实。
原来老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蓝布香囊上的“安”字,是菊花酒里的岁月味,是登高时扶着长辈的胳膊,是饭桌上递过去的一块热糕。这过了两千多年的重阳,把感恩、祈福、风雅、孝亲都藏在一餐一饭、一言一行里,让传统在日子里慢慢淌,越久越香。



 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