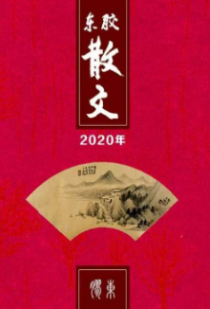
老宅是我生命的源头,人生的起点,庭院是我成长的摇篮。
每每回到老宅,在给花草树木浇浇水,修剪一下枝条,清除满院的落叶时,常与母亲、兄弟们谈及老宅的旧时模样,无不为时光易逝,人生易老而嗟叹。
老宅有南北两栋房子,青石为基,青砖抱户,小瓦叩顶。房内梁、柁、檩、椽样样俱全,粗细相同,颜色统一,格栅窗牖,附带雨搭,黑漆木门,门槛厚重,清一色的东北老红松料。
北栋房子为民国二年(1912)所建,南栋稍早一些,至今已逾百年,从来没有翻修过。
除两栋房子之间的院子较小外,南院、北院都很阔大,房本上登记的面积是九分多地。
南院有一三间的东厢房,是老辈人的磨坊。小时候我曾帮母亲推过磨,再后来,这盘磨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北院临近街门处,有一厦子,平日里存放些柴草等杂物。小院则是祖母养鸡的专用地,父亲在生产队种甜瓜的那几年,我常在瓜田里抓那些大个的黑色甲虫,用瓶子装了,傍晚回家后给鸡们增加一些蛋白质。
院子里绿树成荫,花草盈庭。高树中属香椿最多,小院有两棵,北院靠西墙有一排,皆有碗口粗细。大集体时代,香椿可是当家的好东西。除了开春发芽时,爬上墙头掰下来一些,用面和了,放在锅里煎些香椿饼尝尝鲜外,大都是在其将老非老时,掰下来,用粗盐揉搓变色,放在坛子里密封发酵,待吃面条、喝面片汤时,将其取出剁成碎末佐餐,那可是绝配。
数量居第二位的当属石榴了,三个院落均有种植。南院厢房旁有棵甜石榴,树冠颇大,遮蔽了厢房和正房的窗户。与之对应,在猪圈旁则高耸着另一棵石榴树,树冠虽不大,但难得的是那是一棵酸石榴。
五月浅夏,石榴花悄然登场,宛如精致的红灯笼,挂满枝头。那情形,恰如唐代王翰所书:“牡丹开罢到群芳,一种仙葩更异常。雨浥繁英鸡帻碎,风梳密叶翠翊长。舞裙偏爱分腥血,笑靥应知姑射香。庭院开时多爱惜,莫叫秋信到银床。”
“榴枝婀娜榴头繁,榴膜轻明榴子鲜。可羡瑶池碧桃树,碧桃红颊一千年。(”唐·李商隐)仲秋时节,石榴开始露出红颜,开口笑了。透过那薄薄的榴膜,排排绯红的石榴子晶莹剔透,轻拨几粒,放入口中,香甜可口。
石榴不仅是馈赠亲友的佳品,更是母亲八月十五供奉月婆婆的佳果之一。
其实更值得一书的是北院那棵梧桐树,树干粗大笔直,一个成人也搂抱不过来。树冠蓊郁茂盛,遮蔽了大半个院子。上学放学的路上,或是在山上拾草剜菜,回望村庄,远远地就可看到这棵高大的梧桐树。
梧桐树不仅是家的坐标,还是麻雀的天堂。晨间欢唱,催人早起,傍晚归巢,叽喳一阵,便与人共入梦乡。
但有一年,这种平静被村中的一位退役军人打破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傍晚,酷暑难耐,一家人吃罢晚饭,正摇着蒲扇在街门口坐着聊天。梧桐树上,成群的麻雀正叽叽喳喳地叫着正欢。这时,那位退役军人手提一把气枪走进了院子,后面,跟着他那位与我同龄的儿子,一手拿手电筒,一手提着一个小水桶。儿子用手电光在树叶间搜寻着,父亲端枪瞄准,只要被光柱罩住的麻雀,几乎没有逃掉的,枪枪不落,不大一会儿,就打下了小半桶。要知道,那可是缺油少肉的年代,那半桶麻雀让我记忆了一辈子。
除了香椿、石榴和梧桐,庭院中还植有桃树、苹果、樱桃、家枣、丁香等。有一年,父亲还在桃树间栽种了草莓,在地面上蔓生。树隙间,还栽种了月季、百合、芍药、绣球等花卉。春夏秋三季,可谓花有时,果有令,小小庭院,一派生机盎然。
小时候的庭院时光无疑是快乐的。在这里,见过蚂蚁打群架后积尸遍野的惨烈,探究过水缸穿裙的原因,也用手指探摸过房檐底下水窝的深度,感受到了水滴石穿的力量。还刮过大雨过后桃树流淌的树胶,抢食过阵风过后落地的樱桃。
庭院中也留下了一些糗事和趣事。
一夏日上午,我们兄弟与伙伴们在北院中玩耍,玩着玩着就钻进了临街的厦子,厦子里有一领废旧的炕席,卷成筒状,随意地丢弃在柴草堆上。不知是谁冒出了一句:“在这里睡一觉,也挺美的啊。”随后我们就上了街,在村头沟渠旁玩了大半天,临近午饭时才回家。刚进家门,祖母劈头就问,“老四哪里去了,快快去找找!”我赶紧到平日里我们常去玩的地方找了一个遍,也不见四弟的影子。待我悻悻地返回家里,就见到四弟睡眼惺忪地站在祖母身旁。原来,趁我们几个大孩子不注意,四弟果真钻进了炕席筒里,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睡醒了,就自己钻了出来,让大人小孩虚惊一场。
每年春天,父亲都会在集上抓一只小猪仔,散养在南院子里,猪食槽就放在厢房门口的石榴树下。无人时,常有成群的麻雀落到猪食槽旁,叽叽喳喳地抢夺食物。我曾学着鲁迅,用一短棍撑起筛子,筛子下撒一把麦粒,再用一根长长的绳子,一头拴住短棍,另一头从猫洞眼里拖进屋内,将门关紧,人趴在门缝处,一动不动,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
从门缝里望去,麻雀们只在猪食槽内外觅食,对我撒下去的麦粒丝毫不感兴趣。或许是麻雀们识破了我这小小的机关,或许是听到了我的呼吸或肢体发出的轻微声音。因为我知道,麻雀确实能接收到我们人类感觉不到的声波。
后来,我改变了策略,先到生产队的草垛旁,扒开玉米秸,抓一些玉米螟虫,用母亲用过的雪花膏小铁盒装了。然后,在猪食槽旁,麻雀常落脚的地方,铲上几锨土。每早上学前,支起几盘老鼠夹子,用玉米螟虫作饵,埋进土堆里,做好伪装。中午放学后第一时间冲进南院,还别说,真还屡有收获。
老宅庭院也记录了父母亲的辛劳。北院的房檐下,自我记事起,就摆放着一排酱菜缸和坛子,那是每年小雪过后,萝卜白菜等分到家里,母亲就会把萝卜、芥菜疙瘩洗干净后,一分为二切开,外加一些白菜帮、白菜根,用粗盐和酱油腌制起来,那是全家饭桌上不可或缺的佐餐菜肴,可一直吃到来年的伏天。
冬雪消融,田野里的小草刚露出头,庭院中的树隙间,花丛上,便晾满了母亲打好的衣褙,窗台上摆满了已缝制好的鞋帮,纳好的鞋底,那是母亲为全家七口人过年时要穿的棉鞋做的准备。
大年初一,当我们哥四个排着队到街坊邻右家拜年时,人家看我们身穿清一色新的棉衣棉裤,脚踏白底黑帮条绒面料的棉布鞋时,无不由衷地称赞:“你妈的手真巧!你妈妈真了不起!”我知道,那是人们对母亲一年中不舍昼夜辛苦付出的褒奖。
擦地瓜、晒粉团,煮黄豆、熬酱油;炎炎夏日,小院藤架上挂满的黄瓜、茄子;夏末秋初,厦子上那个硕大的白嫩葫芦,在某天中午变成了软糯的盘中美食;还有那秋风凉收获的梅豆,虽然吃起来有股怪味,但与虾酱拌和在一起,却成了下饭神器。母亲操持的一箪一食,让年幼的我增长了见识的同时,也使人感叹小农经济时代人们生活的辛劳与不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小院的面貌也焕然一新。从小就走惯的青石板路以及路两旁的樱桃、苹果、枣树等消失不见了,那棵高大挺拔的梧桐树也不知变成了哪位新嫁娘的箱柜嫁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长约8米、宽约5米的水泥场,那是为晾晒粮食不得不为的措施。即便如此,那棵每到春天就芳香浓郁溢满庭院的丁香树却被刻意保留了下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兄弟几个陆续成婚,侄子、侄女、女儿相继来到人间,小小的庭院也逐渐热闹起来。
农忙时节,时常回家帮父母收拾庄稼,水泥场上晒满了麦粒、玉米、花生等。伏季农闲,水泥场又成了母亲看孩子、缝制被褥的最佳处所。
周末,先到市场转一圈,什么时令的水果、新鲜的蔬菜、母亲爱吃的年糕等等,都要买一点儿,但,第一选择还是买鱼。每逢推开家门,看到最多的场景是,母亲在水泥场上铺一领炕席,女儿、侄女在上面玩耍,母亲呢则坐在一旁,戴着老花镜,或作着针线活,或做着其他营生,眼睛会不时地往两个孙女身上瞟上几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父亲呢,则一如既往地伏在炕沿上,不是看书,就是写字。
见我买了鱼,父亲便放下书本,习惯性地走到屋檐下,取出那只洗鱼专用的瓦盆来,放到那棵有几十年树龄的丁香树下,然后提来水,便开始了洗鱼。父亲洗鱼总是慢慢腾腾的,首先用剪刀将鱼鳞一条一条地刮干净,剪掉鱼鳍,然后开膛破肚,去腮,再用手指将鱼的内脏去除干净……而每当父亲洗鱼时,我也总是搬个小板凳,坐在父亲的对面,看着父亲的一举一动,间或,帮父亲舀舀清水、倒到脏水,而此时,我们也拉开了话匣。父亲最爱问的一句话就是:“城里最近都有什么新闻?”而我最关心的就是:“家里最近都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二老的身体如何?”等等。
一座百年老屋,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里,白色的丁香花正盛开,浓郁的花香沁人心脾;树影下,一位慈祥的老人正在洗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对面,儿子正平静地端详着父亲,而他们身边,是正在嬉戏打闹的孩子们……
带领着孙男娣女,端午节包粽子,七月七磕巧果、八月十五供奉月亮婆婆,还有到山上撸槐树花,三伏天里粘知了,这一幕幕情景,年年都在庭院中上演。
四弟结婚前,颇重风水的父亲在北院贴着东墙砌起了三间厢房,院子的面貌又为之一变。西墙边引种了两棵紫藤,北墙下移栽了一排毛竹,更奇怪的是,街门旁自己发出了一棵凌霄。
父亲一生博闻强记,手不释卷,颇有一些书法功底,尤擅小楷,又通一些堪舆学知识,对文物鉴赏也有一定的研究。闲暇时分,父亲不是在家看书,就是在练习书法,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诸葛亮的《出师表》、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等,都是其拿得出手馈赠亲友的作品。
自工作以后,一直到父亲去世前夕,《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鉴定与鉴赏》《收藏》等刊物几乎年年都订,周末带回家,为父亲提供了一周的精神食粮。
家中访客不断。有家中添丁的,请父亲算一下生辰八字,起一个吉利名字的;有一些古董贩子,走街串户收了一些好东西,请父亲帮忙掌掌眼的;还有闯关东的后辈人,归乡寻祖找辈分的;还有修房盖屋,来请父亲帮忙开门的等等。
偶尔,父亲也出外访友,多是一些书法绘画爱好者。董其昌的书法,沈化龙的竹子,都是他们百谈不厌的话题。坐在父亲身侧,看他们小心啜茶,小口抿酒,谈兴正浓时眉开眼笑的得意模样,刘禹锡的那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名言佳句便在心中悠然而起。
岁月逐渐压弯了父母的腰脊,蹒跚了他们的脚步。田里的农活再也干不动了,于是莳花弄草成了母亲生活的主题,读书写字是父亲每天的主旋律,街门口的水泥台则成了父母与街坊邻居谈天说地的道场。
院中的花草树木,则在上演着四季轮回:
“绿云堆里紫藤长,几度春风过画堂。”这是仲春时节的紫藤;
“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这是立夏之后的蔷薇;
“凌霄一树竞开花,灿烂明丽放喇叭。姹紫嫣红珠泪湛,光线艳梅眼球扎。署前饱赏花英秀,秋后欣羡绿豆荚。”这是能从夏开到秋的凌霄花。
还有不甘寂寞的鸟雀们。南来北往的燕子,留鸟麻雀,还有头顶白冠的白头翁们,几度在树隙间、屋檐下做窝。
虽经多次劝说,年迈的父母也不肯跟随我们进城生活。没有办法,弟兄们经过协商,决定在老宅安装土暖气,装上空调,在院中砌上带车库的三间平房,安上太阳能,以此来尽点孝心,改善一下他们的居住条件。至此,老宅庭院才定格为今天的模样。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年少时,每当回家,我总是脚步匆匆,因为我知道,家中的餐桌上,永远有母亲为我准备的可口饭菜。中年以后,再回家时,我却走得很慢,很慢,因为我要把雨水、汗水、泪水都拧干在门外。无论世界多暗,风雨多大,我总藏着一枚太阳,在胸口,在眼底,在推开门的一刹那,就轻轻地让它亮起来。
老宅庭院在我的骨血里注入了生命的基因,赋予了我一个挺拔的脊梁,栉风沐雨,身处绝境而从不弯腰;赋予了我一双强壮如铁的脚板,跋山涉水,一山放过一山拦;赋予了我一双明亮的眼睛,阅读人世间的山川美景,世故人情;赋予了我一个宽广的胸怀,宠辱不惊,笑看庭前花开花谢。
世间只有轮回的四季,没有轮回的人生。或许有一天,老宅的烟囱再也不能把炊烟举过树梢,它的门窗也留不住半句争吵或欢笑。但每年春天,庭院里总会钻出几茎倔强的新草,在风里拼命招手,向着街门老巷,向着那个不肯回头的背影。
作者简介: 梁绩科,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人,蓬莱区作家协会副主席,蓬莱区第三实验小学教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写作学会散文写作与评论委员会委员,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签约作家,省写作学会蓬莱创作之家秘书长,烟台市蓬莱区第四届戚继光研究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