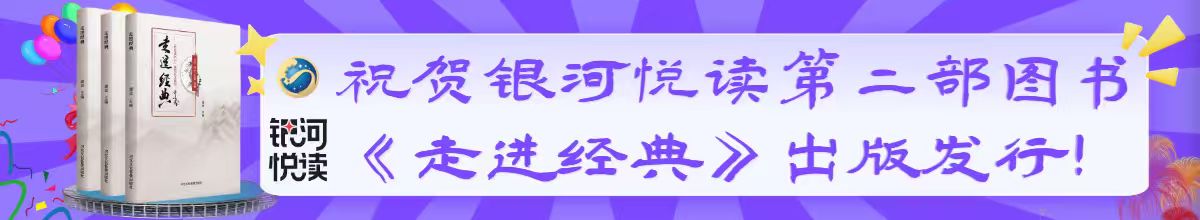1969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父母带着我回到了苏北外婆家,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外婆家是贫农,虽然那里贫穷落后,没有文化,但是那里清静,平和。
外婆住的村子叫小王庄,村上多半姓王。听母亲说,外婆一辈子生十个孩子,有六个还活着,前五个都是男孩子,第六个是我的母亲,四十五岁才生,四十五生个爬山虎,原想可能又是一个崽子,谁知是个没有茶壶嘴的女娃,外婆高兴了。
快到村口了,天也快黑了,母亲显然有些激动,声音都有些颤抖:“快到家啦!到生我养我的地方了。”
这么多年一直忙于工作,根本就没有机会照顾到老人家,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像个丧家犬一样回来了,给她老人家添累来了,心里真不是滋味。
远远地就看到村前的大槐树下,一群人在敲锣打鼓,咣咣采采嘁嘁嚓嚓,这阵锣鼓响,抖擞起了一家人的精神,他们好像是天隔一方的人,欢天喜地地迎接“丧家犬”衣锦还乡。
远远地就看到村前的大槐树下,人群中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扶着一根用旧伞柄改成的拐杖,向这边张望着。她的脚小得仿佛没有脚,好像她的小腿直接戳在了地上。
来了,来了,人群涌了过来,老太太甩掉了拐杖,摇摇摆摆地冲了过来,她快速摆动着的胳膊,但她实际运行的速度却非常缓慢。强忍着一阵急似一阵的心跳,母亲感到双腿沉得几乎拖不动了,泪水不可遏止地往外涌。老太太白发与路边的枯草一样,猛然间也变成了燃烧的火苗子。
“是我的良子回来了,啊,是吗?”老太太说话的声音被她自己的喘息分割成一个个零零碎碎的辞不达意的片断。
母亲哽咽着喊了一声:“妈妈——”便扑到了老太太面前,跪下,脸贴在妈妈凸出的膝盖上。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良子,不哭。”在妈妈面前孩子永远是孩子。
晚上,屋里亮起了一盏四块玻璃插成的罩子灯,洋油烟子从罩子灯上钻眼的铁皮上钻出来。与城里的电灯是没法比,灯光微弱,只能照亮五六米方圆的黑暗。可这是他们家最亮的一盏灯,平日里不用,只有过年时才用。
满满一大屋子的人,外婆在一一作介绍,这是大舅,大舅妈,二舅,二舅妈,三舅……都长得差不多,我一个也看不清,一个也记不得,只是按照妈妈的指点,顺口叫着。
在老家,我们一家受到的依然是尊敬和爱戴,城里 “黑五类”的阴影一扫而光。
在父老乡亲的一致要求下,妈妈在村里开小学初级班,用自己的钱买来了课本,教材。生产队里将旧仓库整理一下,做教室。村上没有上学的孩子全来上学,都在一个班,班上年龄最大十五岁,最小就是我,才六岁。
每家自己带桌椅板凳,到学校统一安排,最小坐在最前面,大板凳当桌子,小板凳当凳子,在这里开始了我一生的学习生涯。
白天孩子们上课,晚上,大人上扫盲班。妈妈忙得不可开交,心情舒畅,脸上呈现着观音般的微笑。她要一辈子扎根在农村干革命,在这里真正感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父亲一回来就被公社请去了,大侦探回来了,还很多案件没有结论,等着他去侦破,过去请也请不到的,父亲身体不好,还是坚持去了。
外婆最疼爱我,常常拉着我说,我们家女孩子精贵。外婆那张干瘦的千沟万壑的脸上深陷的眼窝,有一只眼睛始终打不开,另一只眼,也无精打采的。她凸起的眉骨上竟然没有一根眉毛,仅剩一颗门牙支撑门面,从这扇漏风的门里,唱着她最得意的一首江北小调。
一只呀,小船呀,飘江北呀,
一头又装萝卜,一头又装葱,一头又装女花容。
小呀么小哥哥,什么是萝卜,什么是葱,什么又是女花容?
小呀么小妹妹,红的是萝卜,白的是葱,妹妹就是那女花容……
外婆有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她常偷偷摸摸地拉着我,到她住的房间里,关上门。她伸出枯骨般的手,从一只掉色的木箱里拿出一个红布包,又小心翼翼地从红布包里拿出一个长得很好看的瓷娃娃,对我说:“这是观世音菩萨,会保佑我们全家的。家里有了事,有了难,只要一喊她,她就会立刻过来帮忙,为你排忧解难。”
看到了观世音,外婆左眼那残余的视力,发出虔诚的光芒,她将观音菩萨恭恭敬敬地放在桌子上,拉着我跪拜,双手合十,嘴里念叨着:“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全家,保佑我的良子,保佑……”我觉得好玩,模仿着外婆磕头、祈祷。
据说,在空气中有着亿万种肉眼看不到的原生动物,它们在闪光、在散发出芳香。在外婆的房间内也一样,也有令人心醉的芳香,那是从品德、智慧和习惯中散发出来的最原始、悬凝着一个人内心深处隐而不露的芳香。
我们仰望着观世音那慈祥和霭的面容,祈祷能得到她的庇佑和保护,外婆总是乐于把自己的心愿向她诉说,观世音总是以她默默的微笑回答。
外婆摸着我的头说:“我们家的小仙女方圆,长得慈眉善目,吉人天相,观世音菩萨会保佑你的。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
“妈妈也不能说吗?”在我心中妈妈是最可信任的。
“不能,她是共产党员,不信这个。”过去,村里,家里,大的,小的都有,破四旧全给砸了。这是她偷偷地藏着一个,从她局促不安的神情中,我答应替她坚守秘密。
夏天的夜,寂静而又闷热,外婆家中连窗子都没有,只有一个窗洞。一家人都在外面纳凉。
蝈蝈、蟋蟀和没有睡觉的青蛙、知了,在草丛中、池塘边、树隙上轻轻唱出抒情的歌曲,外婆拉着我坐在她的身边,外婆脱了上衣,裸露的两个奶子像两只风干了的丝瓜,干瘪地挂在胸前。我靠外婆阴凉的膀臂上,外婆用蒲扇拍打着,驱赶着蚊虫。
望着满天的星空,外婆对我说:“做人要有观音菩萨般的心肠,自己委屈点没什么,吃亏长见识,装孙不赊本,敬人敬自己,让人三分不为耻,人心向善,头上老天知道。”
我听得不是太明白,想当初,外婆一定也是这么教育我母亲的。因为。母亲说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德行善,拯世济民,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一个人要有菩萨心肠,这种心肠是和平,是和谐,是博爱,也可以是助人。
我回头看看月光下母亲楚楚动人,美丽、善良、就像观世音。我觉得向母亲学习就可以了,做一个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事,不做坏事。积善行德,要有“菩萨心肠”。观世音的慈悲为怀,成了我最早期的德育教育。
高中毕业了,我要报名上大学读中文专业,圆自己的文学梦。妈妈断然不同意,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当然,她有她的理由,1978年下放知青陆续返城了,小王庄学校的老师越来越少了,妈妈一个人带几个班,实在是忙不过来,本地人能教书的还一时接不上趟,学生就是她最割舍不下的。
妈妈希望女儿留下来当小学教师,妈妈对我说:“方圆啊,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家乡的父老乡亲伸出了最热情的手迎接我们,现在是学校办学最困难的时候,实在不忍心撇开这群孩子不管,你中文学得好又喜欢唱歌,可以在学校教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和全校的唱歌。”
妈妈的焦急、渴求眼光,我明白了,我读懂了母亲对学生的全部的爱,在妈妈的眼里,学生就是她的天,学生就是她的地。
我点点头,应允了。
妈妈说:“好孩子,妈妈耽误你的前程了。”
“妈妈,你说什么呀,邹老师说,有很多著名的作家都没上过大学。”
“孩子,你还小,比其他孩子读书读得早,过两年,等有人接手,你再去考大学。行吗?”妈妈安慰着。
知恩图报,积德行善,善根出善苗,外婆教给妈妈和我的做人的理念,已经融化在血液里了。
那年,我才十六岁就当上了乡村女教师。
大舅妈听说我放弃高考来当老师,拍着大腿叫不平,你妈妈自己当了一辈子的教书匠还没有受罪受够啊?还让孩子去受罪?
“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 继而大舅妈又含着泪拉着我的手:“好外甥女,小王庄的孩子拖累你啦,哪个孩子不听话,告诉我,我去教训他。”
邹老师听说我当上了小学教师,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上写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经说过的话:“花的事业是尊贵的,果实的事业是甜美的,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因为叶的事业是平凡而谦逊的。”
踏上三尺讲台,也就意味着踏上了艰巨而漫长的育人之旅。教师就像那默默奉献的绿叶,时时刻刻衬托着鲜花的娇艳……
外婆大概受到是观世音的保佑吧,一直活了九十二岁。去世后,我拿出那只悄悄珍藏、陪伴她一辈子的瓷观世音放在她的身边。
外婆去世后,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已经无法正常上班了。小王庄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增强了,母亲带着我挥泪告别了家乡的父老乡亲。
外婆在我心里播下的观世音与人为善、慈悲为怀的种子,深深地扎根在我的心中,植于筋骨脉胳,生生不息……
有位作家曾经说过,观世音菩萨与其说是一个宗教的偶像,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力量的物化,一种希望的寄托和信仰的支撑。你可以不信佛教,但你却不能不具有观世音的那种利他精神。从这一点来说,观世音已经走下了高高的神坛,而走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