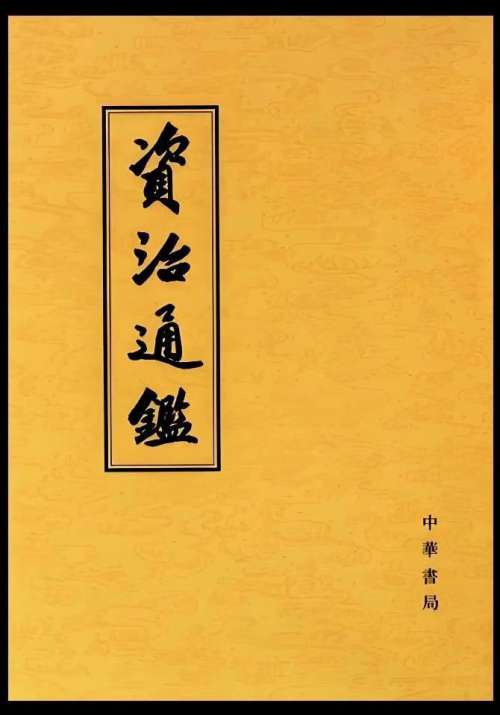
《资治通鉴》多处记载了历代帝王如何选拔人才的经历,也有多处记载执法的问题。我们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出很多有益的经验。卷十四记载了汉文帝选拔人才的故事和如何执法的经历,对我们今天是有启发意义的。原文如下:
初,南阳张释之为骑郎,十年不得调,欲免归。袁盎知其贤而荐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馀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无实,不闻其过,陵迟至于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为口辨而无其实。夫下之化上,疾于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帝曰:“善!”乃不拜啬夫。上就车,诏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于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帝免冠,谢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顷之,至中郎将。
从行至霸陵,上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昔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帝称善。是岁,释之为廷尉。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人有盗高庙坐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选拔人才历来受到执政者十分关切的问题。当初,南阳人张释之担任骑郎,十年都没有得到升迁,他打算辞职回家。袁盎知道他很有才能,就向汉文帝推荐了他,张释之被任命为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出行,登上了养虎的圈舍,汉文帝询问上林尉登记各种禽兽情况的簿册。接连问了十几个问题,上林尉左右看看,一个也答不上来。这时,管理虎圈的啬夫在旁边代替上林尉回答了汉文帝的提问,对汉文帝所问的禽兽簿册上的情况答得很详尽,汉文帝想借此考察他的能力,他对答如流,没有穷尽。汉文帝说:“官吏不就应该像这样吗!上林尉真是无能!”于是下诏让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过了很久才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怎样的人呢?”汉文帝说:“是忠厚的长者。”张释之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又是怎样的人呢?”汉文帝又说:“也是忠厚的长者。”张释之说:“绛侯、东阳侯被称作忠厚的长者,可这两个人议论事情时都不善于言谈,难道要让人们去效法这个喋喋不休、伶牙俐齿的啬夫吗?况且秦朝因为任用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吏,官吏们争着以办事迅急、苛刻督责来相互标榜。它的弊病,就是只有形式而没有实际内容,皇帝听不到自己的过失,国势日益衰落,最终走向土崩瓦解。如今陛下因为啬夫能言善辩就越级提拔他,我担心天下人会随风附和,争相追求能言善辩而不注重实际才能。下面的人受到上面的影响,比影子随形、回声响应还要快,所以您的举措不可不慎重啊。”汉文帝说:“说得好!”于是就没有任命啬夫为上林令。汉文帝上车后,下诏让张释之陪乘。车子缓缓前行,汉文帝询问张释之秦朝的弊病,张释之都照实详细地作了回答。到了皇宫,汉文帝任命张释之为公车令。
不久,太子与梁王同乘一辆车入朝,经过司马门时没有下车。于是张释之追上去拦住了太子、梁王,不让他们进入殿门,并弹劾他们“经过公门不下车,犯了不敬之罪”,上奏给汉文帝。薄太后听说了这件事,汉文帝摘下帽子,向太后谢罪,说自己教导儿子不严谨。薄太后于是派使者秉承她的旨意赦免了太子、梁王,他们才得以进入宫中。汉文帝因此认为张释之很不寻常,任命他为中大夫;不久,又升任中郎将。
张释之跟随汉文帝到了霸陵,汉文帝对群臣说:“唉!用北山的石头做外椁,把麻絮切碎,用漆粘在石缝间,这样难道还能被打开吗!”左右的人都说:“对!”张释之说:“如果里面有让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把南山封得严严实实也还是会有缝隙;如果里面没有让人想要的东西,即使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汉文帝称赞他说得好。这一年,张释之被任命为廷尉。汉文帝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跑出来,皇帝乘坐的车马受了惊。于是派骑兵把那人逮捕,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奏报判决结果:“这个人违反了清道戒严的规定,应判处罚金。”汉文帝发怒说:“这个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性情温和,要是别的马,不就会使我受伤了吗!可是廷尉却只判他罚金。”张释之说:“法律是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是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在当时,陛下派人把他杀了也就罢了。现在已经把他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有了偏差,天下人用法就会随之或轻或重,百姓们该怎么办呢!希望陛下明察。”汉文帝过了很久才说:“廷尉的判决是对的。”
后来有人偷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被抓获了;汉文帝大怒,把这件事交给廷尉治罪。张释之按照“盗窃宗庙供用器物”的罪名奏报判处结果:斩首示众。汉文帝非常生气地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盗窃先帝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是想要灭他全族;而你却按照法律条文奏报判处结果,这不是我用来恭敬承奉宗庙的本意。”张释之摘下帽子叩头谢罪说:“按照法律这样判已经足够了。况且同样的罪名,也要根据情节的轻重程度来区别量刑。现在因为盗窃宗庙的器物就灭他全族,如果万一有愚蠢的百姓拿了长陵上的一捧土,陛下您又将怎样加重对他的处罚呢?”汉文帝于是禀告薄太后,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这段话告诉我们,选拔人才重实质而非口才。汉文帝最初想因啬夫能言善辩而提拔他,但张释之提醒不能只看口才,更应注重实质才能和品德。在现代社会,选拔人才也不能被表面的能说会道所迷惑,要考察其实际工作能力、责任心和道德品质,避免只看重表面的沟通能力而忽视了其他重要素质。张释之指出下面的人会很快效仿上面的行为,所以君主的举措必须慎重。对于管理者或领导者来说,自己的行为和决策会对下属或民众产生深远影响,因此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身作则,做出正确的示范。
张释之在处理案件时,始终坚持法律的公平公正,即使面对皇帝的不满,也据理力争。这启示我们,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的重要保障,无论面对何种情况,都应尊重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不能因权贵或个人情感而随意改变法律的执行标准。在处理盗窃宗庙器物的案件时,张释之考虑到如果因该案件过度重判,会给后续类似案件的处理带来难题,可能导致法律的不合理运用。这提醒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法律时,要全面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影响,避免出现不合理或无法自洽的情况。
二〇二五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