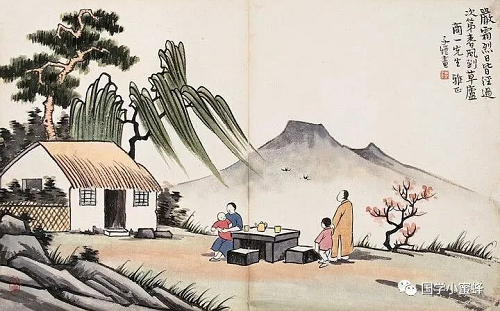
妈妈总是说,“英英,去睡一会,嗯?”说的实在太多了,小英有时候就不耐烦,斜瞅母亲一眼,“我哪有那么多瞌睡!”但可怜的母亲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女儿不知为什么整天心思重重,一点也提不起精神。才十八岁的娃嘛,这叫妈妈的怎么不担心呢。他们曾到镇上看过医生,也说没有什么病,结果闹得小英自己也觉得中了什么邪了——她奇怪自己的脑袋怎么会不听自己使唤,总爱胡思乱想;盯着一件东西,她能乱七八糟地想上好半天;她觉得随便什么人都比自己强,人家总是有说有笑地,可自己为什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呢。街巷里有一群孩子在玩过家家,叽叽喳喳的声音实在讨人喜爱,她的思绪就溜回了童年时光……那是多么开心快乐的时光呀!她真后悔曾经盼着长大,人长大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烦恼呢?她感觉自己活得实在不带劲,吃饭干活,干活吃饭,这有什么意思呢?在庄稼地里忙碌时,她会明显感到头部沉沉地,脑袋似乎还隐隐作痛。想到这样下去嫁也嫁不出去,就难免急出一身冷汗。
这是初冬时节,太阳暖暖地照在当院。小英把家中仅存的一点籽棉晾晒在竹帘上,准备换点钱给哥哥寄去。她很羡慕哥哥能在大学里求学深造,将来就是稳拿工资的城里人。她后悔自己停学过早,可那时知道什么呢,村里一拨同学大都不是一个样嘛;而且父母年事已高,刚刚分到户的责任田总要有人种呀。尽管凭着父亲的一身农作本事,这几年收成还不错,可家里总是缺钱花,供哥哥一个人上学已经不容易了——庭院里稀疏地散落着枯叶,一只老母鸡在咕咕叫着四处觅食。如果不是那头不听话的大黑猪,这棉花本是不必看守的;这时候那家伙正无所事事,躺在东墙下毫无理由地呻吟着。收音机里正在播放电影录音剪辑,小英正好可以坐下来,一边纳鞋底,一边留心听着。她感觉这样可以把头脑占住,会少一点烦恼。事实上,她对什么节目都感兴趣,她觉得总能从中得到一点收获。正像一边干活一边想心思那样,听收音机这个时髦的东西早已成了她的习惯了。妈妈在院子里来回忙着,她不太能听懂里边的声音,总是埋怨,“你不是说头痛吗,歇一会多好,成天听,不嫌唠人!”小英就是不理她。
同巷里一起长大的芳芳来了,一进门就唧唧喳喳说个不停。“喂,你也不出去转转,真是个好人,就知道做活,该不是给未来的郎君做鞋的吧,呵呵呵——杨婶,现在街上可真是越来越热闹了,挤都挤不过去。一街两行,排得密密实实,卖什么的都有,还有人把面条搬到街上卖哩。我一看,人家吃的人还很多,你说怪不怪——哎,你猜我刚才见谁了,哎呀呀,风骚得很。晓莉今天穿了一身新,还穿着个前面分叉的男式裤,实在是扎眼!真把自己当城里人了……”
小英双肘枕在膝盖上,似听非听,只是偶尔理理自己的乌发。
她们所说的晓莉,是本村少有的几个高中生之一。因为没有考上大学,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了一阵子后,回来便在镇上开了个裁缝部。村里没有多少人关心她的手艺究竟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多多少少觉得这女子有点不正干。所以即使真想做衣服了,都要绕道去照顾别人的生意——谁知道为什么这几年一下子冒出了这么多裁缝店!?哎,人们都是这样,总觉得自己身边的人不会有、也不该有什么大出息。人们还相信这个特别爱打扮的漂亮姑娘爱和男人胡搅瞎混。“谁说得准呢”,起先是几个妇女交头接耳,后来是七邻八舍都乐于相信了。有人还指出,某天晚上,自己就在村头麦积堆里看见过什么。这类事实不断地增加,于是大家都对晓莉一家人表示惋惜了,“父母都是本本分分的人么!”
但是说心里话,小英还是挺佩服这晓莉的。是呀,人家在镇上自己开店,像个工人似的,日子有奔头了。可自己有什么,成天守在地里,料理刚刚分到手的几亩地,看起来务实本分,左右都是夸赞声,也开始有人给她张罗着瞅对象了,可自己就是这么个样子,能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呢?
忽然听到一阵猪娃的尖叫声,是爹爹买回来一头黑猪仔。刚放到院子里,小家伙就腾腾腾,撒腿跑到见不到人的地方去了。爹爹嘿嘿嘿,眯起了眼。“还美着哩吧,嗯,还美着哩吧?”他不断地说,妈妈都回答他了,可是他还要问,好像根本没听见似的。其实这就是爹爹的习惯。尽管这个农活上的多面手有时可以一天不说一句话,但只要他一高兴,例如每当给家里添置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显得特别激动,总想得到家人的夸奖,因而总是先自夸一番。他现在蹲在院阶上,抽着旱烟袋,一五一十地述说着买卖时的经过,无非是一些讨价还价的经验之谈。可小英还是心思沉重地坐着,一点也乐不起来,觉得大家都把她忘记了。杨老汉猛然发现似的喊,“这女子又咋啦……”做妈的也从灶房里出来,唉声叹气地望着女儿。
一直凑在旁边夸赞的芳芳说:“杨老伯,你在街上碰见晓莉了没有,咦,你看那风骚劲儿……”
杨老伯历来也看不上这晓莉,要不然她也许还要做自己的儿媳呢。这会儿他顾不上答话,只是惊恐无措地看着小英。
吃完饭,妈妈劝小英出去走走。可别的地方她实在没有心思去,就来到了前巷堂哥永正家。和村子里不少年轻人一样,这永正在农业社里混了几年,也没有学会多少务农的本事,除了下苦力,就什么也不会了。前几年,凭着自己英俊、秀气还有一点文化,他娶到了一个漂亮的媳妇。可是很不幸,这个“西施枕头”既吃不了苦,针线活一个也拿不起来。结婚不几年,就完全耗尽了做姑娘时的那种伶俐劲儿了。现在一家三口过着窝窝囊囊的日子。奇怪的是竟然会时常停火断炊。小英因此也想到了自己未来的生活。哎,想的太多了吧。
永正哥一家正在吃午饭,常年的忧愁和独立生活的磨难,已经让他学会了老辈们的长久沉默。看见小英,倒很热情,而且近乎迂腐地固执,硬要她尝尝自家的饭菜。“西施枕头”坐在门槛上,端着碗,嘿嘿地笑着招呼。不谙世事的侄子抱着碗,跑过来,硬要姑姑抱。小英接过湿毛巾,一边给孩子擦着手,一边说:
“你们也该娃喂个猪,搞点副业才能有收入哩。”
“养猪?”谈起正事,永正哥好像就泄了气。“唉,地里的活都忙不完——让谁喂?也没有啥饲料……”
“那喂个养也行呀,只要抽空割点草就行了。”
“看喔懒汉还知道割草”,“西式枕头”向丈夫一瞥,仿佛是在打趣。
生了闷气的永正哥扭身进屋去了。说起买棉花的事,兄嫂好像才忽然想起,“对,对,我也该卖了,快过年了,换点钱。我明天要晒一下,后天咱一起去。听说你哥那同学也管事哩,我也沾点光”。
这天下午两三点多,温热的阳光地照耀着大地,小英、芳芳和兄嫂三人拖起大棉包,骑车行走在凹凸不平的乡间道路上。临出门时,小英在镜前特别打扮了一番,很满意地打起了精神。
“明年我还要种花,现在就是棉花可以换点钱。哎,把地给了咱自己,有时真不知道种点什么好……”?兄嫂一边登车,一边自顾自地念叨着。在两个年轻姑娘面前,她显得有点不自信。
“现在种啥都行,关键要会务弄,成勇家人多地多,人家今年种红薯,今年听说酒卖了两千多块呢,”芳芳说。
“好呀呀,还种红薯,还没把红薯吃够?从小到大一直吃,我说啥都不想吃了。”?兄嫂回应道。
“啥能卖钱,就该种啥,光想着自己吃,哪行呢!”小英刚才一直在想,找到哥哥同学,自己该怎样给人家说话——她其实是从来不愿求人的。这时候她把思绪闪回来,回敬兄嫂道。“可是现在的人好像都不爱种地了,都去学了什么手艺。”
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尽管他也知道,一个女孩子,学手艺一说,自己并不适合。
芳芳说:“学手艺?你快别提了,咱农村人能学个啥嘛,都是跑出去胡混哩。你没听说吗,一队里的军军跑出去一年多,他爸他妈喜滋滋的,还以为他挣了钱回来咧。谁知道他是溜回来的。那一晚上前脚刚进门,后边警察就追来了,话还没说几句,就翻墙跑了。有人说他偷了东西,还有人说他杀了人,谁知道呢。现在外面乱得很。还是人家二队的虎子有本事,在外跑了不到一年,带回来了个四川媳妇。家里弟兄两个穷得学鬼叫呢,喔四川媳妇能呆住?谁知道他靠的是啥本事,呵呵呵,人家都说是骗来的——哎,你说怪不怪,这几年咱村上得怪病的特别多,昨日我妈和我数了一遍,光得脑溢血、半身不遂的就有成十个,年龄还不都不算大。我妈说,现在的人是心累,都是急下的病……”
三人就这样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蹬车。铮铮车轮声,似乎给是她们谈话的伴着奏。说起别人,小英又想,自己该嫁个什么人呢?哥哥说,你爱谁,就和谁结婚。但光有爱也不行呀,爱并不能挣来钱……这些问题老是折磨着她,得不出一点眉目。
这天,卖棉花的人很多,刚进棉绒厂大门,就看见远远地有一群人在无声地活动。她们直接去找小英哥的同学,指望他能帮忙,验个好等级。已经到门口了,芳芳上去敲门,但小英却止住了她。她无目的地愣在了那里,羞得一脸红晕。她心理很乱,可气的是芳芳不住地抱怨。
是从哪一天晚上开始,她感到通宵未眠的呢?小英自己也说不清楚。躺下来,头脑里竟然杂乱地迸起了火花,这又怎么能够睡着!有时候,过了好长时间了,忽而坐起来,头脑竟是冰凉的一片。这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四下里黑漆漆的,爹在打着鼾声,妈妈则断断续续地说着根本听不清的梦话。这使小英感到恐惧!她赶紧又躺下来,把头缩进被窝里,又感到脑袋在隐隐作痛。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但也许还睡过了一阵,要不然怎么会清清楚楚地感到一个男子给自己说过悄悄话?她拨浪鼓一般地晃着头,极力使自己静下来;她紧闭上眼,一二三,慢慢数起了数,但是白费力……忽而是几个同伴表示轻蔑的眼,忽而是一大群男女的讥笑声,仿佛又看到了几个妇女在交头接耳。她清清楚楚地听到人家说她是个小傻瓜,一个什么也不会做的小傻瓜。天色是灰蒙蒙的,好像遍地湿漉漉的,她看见几个秃着头的男女扭打在了一起,又有一群穿着灰色棉袄的秃子指手画脚,在争论着什么;有一个疯老头,看见她就甩着灰色的长袖,跑过来,嘿嘿哈哈地应要拉她走。“啊哈哈——”她大哭起来了,爹妈被惊醒了。
“英英,英英,你到底有啥不对劲呢”,妈妈惊异地喊着,母女俩抱着了一团。爹爹赶紧下炕,燃了一把柴火,举在手中,很虔诚地在屋子里绕了一圈,然后从后院转到前院,打开大门,把不知道什么东西送了出去。还在大门口散了一条灰线。回来时,母女俩还在抹泪,“英英,你梦见啥了,给爹说说”。小英一直哭,她不知道该如何说。
第二天,小英眼圈发黑,原本俊秀素雅的一个人,明显没有了活力,像患过一场大病似的。妈妈给女儿略作打扮,一家三口坐了驴车,起身上医院去了。
到底中了什么邪呢,杨老伯心思沉重地想。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