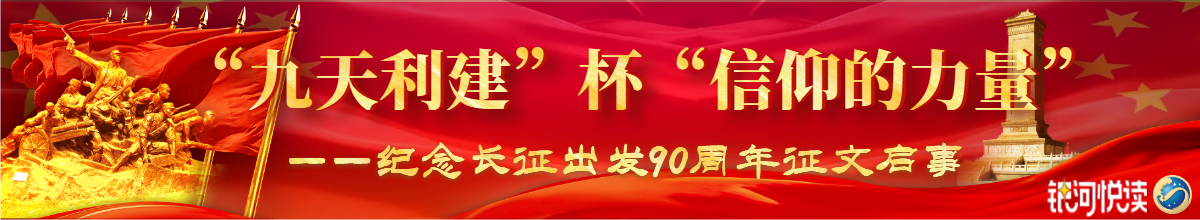(一)
刚在北站的南入口站稳,李占恒老师便主动与我打招呼,当然他是以询问的口气探寻我的身份。李老师的眼力不错,单凭微信群里的头像就认出了我,这或许与他作家身份所具有的独特观察力有关吧。而此行的目标珍宝岛,就是李老师提议的,他要做田野调查,包括俄罗斯的伊曼市。
李老师带给我和丽萍姐两套丛书,书名为《白山黑水三人行》,约有八十多万字。里面描写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有一部分关于珍宝岛战役的采访,是当年参与战役的部分官兵的照片、口述故事,当然最为珍贵的是三位曾立战功的老战士的亲笔签名。
这套丛书幸亏有江洋老师冒险夺回,我把它遗忘在车厢里。我们已经走出列车,阳光从高空抛下,刹那间击醒了我,我大喊不好,一边说出原因,一边往列车上跑去,只听得身后丽萍姐不断惊呼,“依蓉,火车要开了,太危险了。”冲上车厢的一刻,恐惧感忽地窜上来,车厢过道挤满了安放行李的旅客,挤进去拿到书,怕是下不了火车了。我像没事儿似地走下火车,脸上却难掩歉意和羞愧。江洋老师在我下来的一瞬间冲进火车,之后他应该听得到我的尖叫:“老师危险,火车马上开了!”
江洋老师与李占恒老师都是部队当兵出身,而江洋是副师级干部转业,退休后任职散文学会的常务副会长,舞文弄墨,自在快活。当兵的人活得是责任,面对困难首先考虑的是完成任务,而不是保全自我。可对我来说,回到火车上的瞬间是绝望的,我不想对着启动的列车发出难以忍受的尖叫,虽然之后这叫声传递给了江洋老师,有一种浴血其中的震颤,直到江洋老师提着书袋子,下了火车,我才平缓内心的尖锐冲突,随口问了一句:“你身上带着买返程车票的钱吗?”
向北方去,总有一种对于寒冷的担心,行李里自然少不了御寒的衣物。事实与我的判断相反,九月中下旬,虎头依旧可以穿薄裙子,上面要套个长袖衫。
刘恩学老师提着个摄像机,总是转在我们的四周,似乎是寻找捕猎的最佳时机。他要选取角度,拍摄完美作品。刘恩学老师和在哈尔滨车站相遇的白石亮老师,都是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老兵,这次随同我们,一起来看望他们的老战友——在风雨中被石化了近五十年的英烈。
(二)
珍宝岛位于黑龙江虎林市,在饶河县南端的乌苏里江上,占地约两公里长。乌苏里江资源丰富,两岸土地肥沃,原始森林形成一道绿色屏障,珍宝岛依偎其中,在远山淡蓝的光影下,折射出翡翠般的华彩。半圆形水域中心有一块肥沃的绿地,形似元宝,这块绿地被称为珍宝岛。
李占恒老师受邀来到珍宝岛,采访当年战役的真实境况。这次他要写部长篇小说,纪念珍宝岛战役以及当年为国捐躯的英烈们。黑龙江边防参谋长刘国胜热情接待了我们,并陪同我们六人参观,介绍珍宝岛的现况。从他敬礼的姿势,看得出军人的严肃性。他们护卫着我们的国家,使一切危机消散成灰,让同胞们再不会想起战争是什么,一切与死亡、灾难有关的事情将被遗忘。
九月的阳光拉长每一个身影,我们站在209.4高地的山坡上,被山风抚慰得神情荡漾。远处的河面上,珍宝岛犹如一处雕刻品,嵌进大地之中。它使我们的视野无限拉伸,那些活过并在此倒下的人,用身体写下一段永恒的历史,他们并没有远去,他们在岛上安睡,身体被秋风扫得郁郁葱葱。这些抛开命运的人,为激情所燃烧,用无法抑制地冲动,将自己付之一炬,完成最终的使命。
往日的痛苦与今日的幸福直面相对,复杂的情愫交融一起,被自然规律冲淡。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从我们渴望的生命,到看似存在的法则。如今怀念的人已是寥寥无几,最终抵不过一部小说更受人们的关注和热爱。
借着山顶的一处豁口,轮流拍照,把珍宝岛当作聚焦地,我们分别站在一丛绿树的前面,头顶仿佛悬着珍宝岛这颗美玉,它的河床是一条丝带,柔软地延伸向远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是来瞻仰它的美,而是纪念它中国的属性——再也没有因它的身世而引起的口舌之争,以及战争。
和平而温馨的后面,有我们无法想象的故事。走进珍宝岛,六十年代建立的几处营房矗立,斑驳的墙壁长满苔藓,偶尔显露石灰的墙皮,证明它坚实的筋骨。如今这一切成为历史的书稿,几颗子弹曾穿透其间,展示着战争的模样。形销骨立的营房,冷静地站在前卫哨所,接受一种使命,等待世人去翻阅它的沧桑。
越过营房,后面是一座人行桥,架在溪流上。溪水不宽,却在坡度的引力下发出细琐地喧响,引导我们倾听其命运的深处,那不可触摸的悲凉。几位年轻的士兵被刘参谋长叫来,战成一行队列,以军礼的姿势迎接我们。军人的气质是高贵的,即使融入草莽之间,也能渗透出不同寻常之处。这似乎蛊惑了几位作家对于军人生涯的向往,我们煞有介事地借了军帽,戴在头上,与士兵合影,与同行的友人合影。我们希望留住这历史的瞬间,甚至希望能走进去,与端坐在石凳上的英雄杨林交谈,为他写一本传记。
过了小桥,前面是一片沼泽地,上面长满了芦苇,远远的金黄一片。这是秋日的中午,金黄的色泽给人一种丰收的喜悦,尽管没有麦浪的欢呼,尽管那片金黄色的草茎下面布满沼泽,可还是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沼泽地下面是一片雷区,板油马路两侧设有提示板,警示游人不可以进入草莽之间,那是苏军偷袭时留下的地雷,它们深藏于地下,带着死亡的阴影。
刘恩学老师在树丛的旁边,为我们演示他当年参与战斗的过程。那时他们班接到指示,作为先遣部队,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根据当时局势,这一战势在必行,但是我们不能发第一枪,逼迫对方先出击,然后以被迫还击的姿态,将敌人赶出我国的领土——珍宝岛。刘恩学老师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当时,他提着木棒与战友们潜伏在树丛边,萧瑟的寒风刀子一样,切割着几近冻僵了的身体,当敌人的士兵经过眼前,他一个箭步跃起,举木棒打向敌人士兵的后脑勺。敌人非常警觉,被击打的瞬间提起机关枪扫射,一颗子弹从他的左侧腋下进入,穿透胸膛,从后背正中射出去,他应声倒下了。或许冷冻成为麻醉剂,他感觉不到疼痛,眼前只有晃动的人影,枪声、手榴弹声此起彼伏,他听到另一个战友倒下,带着中枪后的痛苦呻吟,那也许是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次叹息,他试图去看清哪个战友,但是身体动弹不得,仿佛与大地凝成一片土壤。接下来的声音混沌在一起,是的,珍宝岛战役正式打响。
白石亮也是同一场战斗的英雄,他担任重炮连的弹药手,在生死考验之间,沉着应战,出色地完成任务,并荣立三等功。之后三年时间,驻守在珍宝岛135.0高地。白老师的军旅生涯要幸运得多,离开野战军后,调到军队院校工作,在国防大学从教期间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尽管时光远去,一些经历被岁月积淀成些许影像,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去,但白老师对往事念念不忘,他先后三次重返珍宝岛,悼念革命烈士,并向陵园捐款,表达对于逝去的战友追忆之情。
谈起当年的战争,两位老师都比较激动,他们在回忆当年那些炮火,还有炮火中丧生的年轻战士。说到死亡,刘恩学老师停顿下来,右手不自觉地按住了左腋下的伤疤。白石亮老师则显得亢奋,那场战争带给他无穷的勇气,仿佛再去消灭一小撮敌人,他才会善罢甘休似的。
白老师是懂政治的人,他对我们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小战而止大战的战斗,它遏制了苏联对我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企图,这次作战胜利,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捍卫国家领土的决心和意志,从而在国际上有了一席之地。”
当我们离开营房哨所,前往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纪念馆,在一尊石像前面,我被一种场面震惊了。刘恩学老师右手提着摄像机,相机的长镜头凸垂下来,仿佛是机关枪在完成扫射过后,无意识地对准地面。他的左手搭在一座石像上面,抚摸着石像的肩膀,与石像相视而立,仿佛在交谈些什么。
那是两个人构成的石像雕刻,坐着的名叫王庆荣,怀里抱着牺牲的战友,他一只手指向前方,仿佛活着,但不具有生命。在他的眼里,是炮火和倒下的战友,是时间不能带走的永恒,他的命运还未终结,在期待战火的熄灭。战争是一场罪孽,让无数的生命披上死亡的外衣,他哭泣死难的兄弟,他活着,用抱紧的姿态,活在别人的视线里,活在精神世界里。
我走上前,想说几句什么,发现刘恩学老师的眼睛模糊一片。我知道这抱在一起的石像,是他当年的弟兄,他们同时上了战场,先后被抬下前线,可如今面对面地相望,却是两个世界的人。
接近傍晚的风凉爽起来,像是突然染上了疾病,令暮色呈现出不安。我们参观完纪念馆,途经广场前面,又见到刘恩学老师的背影,正面对那座石像,用手抚摸着兄弟的头和脸颊。他一定是忘记了带酒,因而感到些许惆怅,他一定说出很多想说的话,但这些声音隐匿于自然之中,唯风风雨雨能吹出它的韵律。
(三)
从虎林出发,乘坐大客车,向列索和伊曼进军。
这次来俄罗斯伊曼市,同样是缘于珍宝岛战争这个题材。在虎林国际旅行社的安排下,伊曼市市长派两位市政人员陪同我们,参观当地博物馆、纪念碑、以及艺术学校等有特色的地方。
早年从哈尔滨遗留下来的建筑中,欣赏俄罗斯对于建筑的艺术构思,以及创造能力,误以为俄罗斯独特的建筑工艺,会使它的每座城市到处呈现华丽的古堡。随处可见曲线玲珑的外部形态,开阔明朗的内部构造,以及一些有着大师风范的人,外套一件长风衣,戴着礼帽,深邃的眼神飘出异样的神采。他们漫无目的从古堡下走过,令一切自然之象都融入艺术的本身。而古堡穿过岁月的风尘,抖擞出历史的烟云,在集体注视下,犹如一列小火车,驶进游子的视野,辟出一幅幅画卷。
然而我们大吃一惊,伊曼市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这座小城以充满讥讽的命运,对百年前沙俄兴建哈尔滨的铁路及建筑,做出一种调侃的演说。那些敦实厚重的木刻楞房子,呈现出老年人的灰土气息,剥蚀的外墙面犹如下垂的脂肪,坚守生命几近枯竭的部分。很难见到近新的建筑,多数都已经达到近百年的历史。时代变了,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变化一新,可伊曼市还蜷缩在七八十年代的叹息里,斑驳的油漆犹如历史的年轮,被秋风一代代狂扫。
马丽萍姐姐身穿一袭红裙,在伊曼市萧瑟的秋风中,点燃了一把火。在我们进入艺术学校,与俄罗斯的大眼高鼻梁的娃娃们拍照时,红裙抢足了风头。孩子们个个神采飞扬,对我们的到访感到意外和惊喜。
博物馆陈列着不知何年何月的老物件,它们在集体袒露一种沧桑,与红裙的乍然相遇,显得无奈而落寞。这座博物馆是多元化的,除了旧物展示之外,还展览艺术品、手工制品、宗教文化,在其中一间较大的展厅,展示战争的图片,旁边有大段的俄罗斯文字解释,紧邻的墙壁挂着几十位殉难将领的头像,下面都有详细的个人简介。这些不同范畴的展品,陈列在不同的小房间内,有些拥挤,简陋之处出乎我们的意料。
在谈及博物馆陈列的珍宝岛战争画卷的一幕时,俄罗斯讲解员微笑片刻,歉意地看着我们说:“我应该怎样介绍呢?我不想说出你们不愿听的话题,同样我也不想说违心的话,战争是残酷的,但愿这次战争是最后一次,永远不要再有。”她不想解释战争带给了他们什么,这恰巧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事。那种解释一旦说出,应该不是我们想要的正确答案,这一点她很清楚。但是她把那种答案当作唯一真理,在遇到寻求真理的人到来时,加以善意地隐瞒。
要说具有欧式风情之处,还属列索市的东正教堂,半圆形穹顶,十字架,用头巾包住头部并穿长裙的朝拜的妇女,其他就没什么特别之处了。在伊曼和列索,我们见到许多纪念碑,纪念曾经的战斗英雄,一些墓碑前摆放着鲜花,据说当地的百姓对英雄无比地崇敬,凡路过石碑,要摘取一束鲜花置于碑前,以示敬意。
中国人对于死者的亡灵充满敬畏,缘于传闻中对亡灵的恐惧——相信其能暗中操纵人类的命运。虽有敬畏,但恭敬并不随处可见,鲜花也只有节日才可见到,更多的是敬而远之。俄罗斯对于英雄的亡灵是发自内心的崇敬,并不惧怕。死者纪念碑常立于市中心的广场,即使坐落于郊外,只要有路过的人,就会有鲜花放于碑前。这意味着他们热爱英雄,或者渴望成为英雄。也许他们并不热衷于思考死亡,并未吝惜于客居尘世的生命,战争能燃起某些善战人士的激情,他们潜伏在拥挤的穹庐之下,蓄意消耗生命的本能。
我们从列索市出发到伊曼,最后又回到列索,在一家指定的餐厅里享用了俄式风味,烤肉的味道很适合我的胃口,估计同行的其他几位老师也很受用。据说这是当地最好的一家餐厅,除了本地人喜欢来此之外,更多的顾客是中国人。这一餐美味是值得回味的,是此行来俄罗斯留给我的最好印记,是幸福的一个体验。人们根据感觉需要来判断幸福的标准,比如这个明朗的秋日午后,我们什么都不想做,只需要晒晒太阳,世界就那么美好。
我想我们的离去并不带走什么,我们的到来也不会留下什么,所有人的命运被挤进一本巨作里面,呼唤和平是是这本巨作的中心议题,是人类发出的共同的声音。可是总有那么一些时段,有些声音变得沙哑,犹如一件衣服,脱离了主人的骨架,虚无而空洞地倒下。人类习惯于与外界为敌,而有时在利益与欲望猛戳你的内心时,也会与自己为敌,背叛最初的誓言。
秋风一代代狂扫,历史终归会还原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