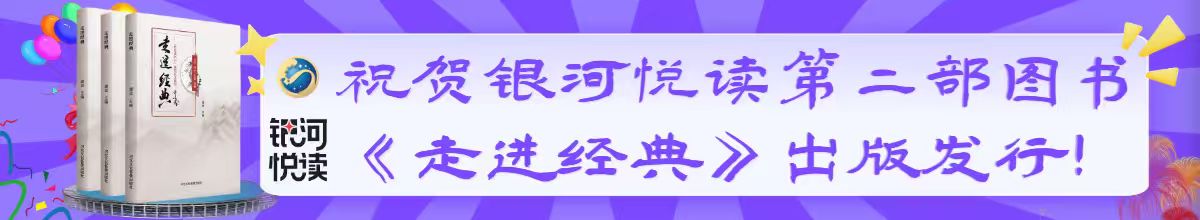记得有人说过:好男儿志在四方。但无论走到哪里,故乡,永远是我们的根儿,家,永远是我们灵魂的归所。前段时间,弟弟打电话告诉我:我农村老家十几年前盖的那四间水泥预制板房屋漏雨了,让我抽时间回去重新处理一下。于是,国庆小长假专程回到老家,开始备料。然后在村里找了十来个壮劳力。只两天半时间,四间房顶就修好了。当我按照目前的市场价给他们付劳务费时,他们都一一拒绝了。特别是那个叫任四平的小伙子当时说的那段话,让我感动不已,终生难忘。“叔叔!我们从小学就听过你的事迹报告,你为了民族的尊严,祖国领土的完整,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勇敢杀敌,多次立功受奖!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能为您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是我们最大的荣幸……”此时此刻,又让我回忆起小时候家里盖房、打坯、打房顶、垒墙头找人攒忙的情景。那热闹、温馨、亲切、快乐的场面,至今依然历历在目,清晰如昨!
据史料记载:“攒忙”一词距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它是黄河文明的一个佐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的老家,曾广泛流行着一种义务帮工形式——攒忙。说起攒忙,那可是庄户人家有了大事小情之后,乡亲们不讲条件、不计报酬、相互帮助共同完成的一种互助形式。虽然没有组织、没有报酬,没有招待,但大家都乐此不疲,无怨无悔!童年时,老家乡亲们之间相互攒忙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无论谁家兴工盖房、谁家垒墙头、建大门,谁家结婚娶媳妇、送闺女、谁家有病有灾了,只要人们听说或知道后,就自发组织来帮忙,完成任务后不吃饭,不喝酒,各自回家,没有任何怨言。攒忙,是一种人类体现大爱的友善行为,正是攒忙这种纯朴的互助形式,让人们体味了乡情的厚重,使人们在互相帮助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折射出一种淳厚的村风民俗。我母亲不仅是庄稼地里的一把好手,爱琢磨,能吃苦,还有一双巧手。她不仅会种庄稼、纺线织布,还会裁剪衣服,剪纸、绣花,在村里那可是响当当的“能人”。在我的记忆里,尽管家里很穷,但因有个勤快贤惠的母亲,我们姊妹五个,平时人人穿得有模有样,常常还让邻居家的孩子们羡慕嫉妒呢?这不!母亲经常给村里的乡亲们攒忙,无论多忙都有求必应。隔长不短,村里的婶子大娘们拿着布料来到我家,向母亲请教剪裁衣服的技术,每次她总是耐心讲解,现场示范,还手把手地传技术,一招一式教方法,直到大家学会为止。母亲不仅心灵手巧,还特别热心肠。平时,村子里有不少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拿着布料来让母亲裁剪、缝制,热心肠的她从不拒绝,总是认认真真地裁剪好。遇上那些家里没有缝纫机和不会做衣服的,母亲总是贴着功夫儿和针线帮人家做好。为此,母亲和邻里的关系处的非常融洽,无论谁家有了困难都会伸出援救之手给以帮助。她这种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乡亲们的一致好评。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每代人有每代人印记。是啊,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没有更高的奢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纯朴无暇。那时候的乡亲们都是古道热肠,一家有事,大家都热情帮助。诸如:谁家要盖房了,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不大会儿功夫,全村人几乎都知道了,开工建房那天,乡亲们一吃过早饭,就三个一群儿,五个一伙儿主动前来帮忙。大家伙有用大镐、铁锨挖地槽的,有用小拉车运土的;有挑水和泥的;有搬土坯、木桩的;有调理大梁、檩条的等等。大家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忙得不亦乐乎。因那时庄稼人都不富裕,主家只烧几壶白开水,备上几盒烟卷。渴了,就“咕咚,咕咚”喝碗凉白开;烟瘾来了,就边干活边抽上几口烟卷儿解解闷儿!到了中午和晚上,攒忙的人们不顾一天的劳累,放下工具,就各自回自己家里吃饭去了,没有一个喊苦叫累的。大家感到,能为乡亲们尽一点微薄之力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谁都没有怨言。
那个年月,起房盖屋是庄户人家最大的一件事情,需要乡亲们来攒忙。动工前,主人家往往要请“算命先生”择好吉日后才开始破土动工。我十岁那年,因家境贫寒,靠东挪西借才勉强盖了三间土坯房。记得我家将土坯,大梁、檩条、椽子等备好后就开始打地基。父亲首先请来村里的四名瓦匠高手,用尺子丈量好长和宽的距离,根据宅基地的大小,设计出需要打夯的位置,用白石灰划出承重山墙的部位。然后再按着白灰划出的位置,挖出一米来宽、半米深浅的地槽,灌进水,待水沉下就可以打夯了。那年,我家盖房用的就是木夯。那天,父亲请了20多个的壮劳力,分成5个班,一班为4人,轮班打夯夯实地基,一直打到凌晨十二点地基才打好,攒忙的乡亲们只喝了几碗白开水就各自回家了。我为乡亲们的质朴、善良、淳厚深深地感动着!
地基打好以后,就开始垒大墙。于是,父亲又从村里找来了20多个壮劳力到我家攒忙。大家各有分工,有和泥的,有运泥的,有搬土坯的,有垒墙的,大家各负其责,非常卖劲儿!你看!那和泥的小伙子儿,将花秸扔到泥里后,光着脚丫子在花秸泥中来回踩踏,有的双脚冻得通红通红,有的双脚被玻璃扎破也不吭一声,一直把花秸泥和好为止;你瞧!那运泥的小伙子们,有的用铁锨端,有的用脸盆来回不停地搬运,汗水一个劲的往下流,也不肯停下来歇一歇;你听,那上了年纪垒墙的老师傅,蹲在一丈高的墙上,一边垒,嘴里还一个劲儿地吆喝着:快来泥呀!赶紧上坯了!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只一天时间,房子的主体墙就垒好了。本来父亲早早就准备了酒菜,等大墙垒好后让乡亲们喝杯薄酒,可大家就是“不领情”,他们简简单单地洗了把手就各自回家了,这感人的一幕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大墙垒好后就开始上大梁,上梁时 首先要用大红纸用毛笔写上:“姜太公到此,上梁大吉大利”!然后将大红纸贴在大梁上,祈求上苍保佑主家安安全全,大吉大利。一阵鞭炮响过之后,前来攒忙的人们用粗绳索绑住大梁的两头,站在上边的人用力将绳子往上拉,站在下边的人们则用铁锨或木棒往上顶,把大梁架好固定后再架檩条。接着,攒忙的人们把一根根椽子均匀地架在檩条上,铺上芦苇帘子,然后在芦苇帘子上铺上一层厚厚的花秸,抹泥的师傅用花秸泥将房顶抹平。据说:上大梁时,现场不能有怀有身孕的妇女,否则,生出来的孩子就成了“颌子”(老家称腭裂叫颌子)听村里老人们讲:俺们村里的郭肖红大婶,在怀孕期间,不经意看到了邻居盖房上大梁时的情景,结果生出来的孩子就成了腭裂。后来,尽管到处求医,做了手术,上颌还是留下了一道疤痕。孩子长大后,媒人先后给他介绍了三四个对象,只因其腭裂没能成功,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当然,这只是农家人一种传说和猜测,至于腭裂是怎样形成的?医学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房子盖好后要及时打房顶。听老一辈人讲,打房顶时,在粘土和花秸中掺上一些老炕坯土容易吸收水,特别结实,还不易漏水。于是,父亲将家里睡了十几年的老土炕给拆了下来。只见老炕坯沾满了做饭烧柴时冒出的烟子,黑酥酥的,特别的结实。父亲和哥哥将土炕拆下来的土坯堆成堆,坯堆好后灌上很多水,闷上一天一宿,土坯遇到水就松解开来,再掺和上新的粘土,石灰,花秸。等把这些东西掺好后,父亲又找来七八个壮劳力,用铁锹,三齿镐来回翻动十几遍,才把一大堆的上房土和好。由于当时机械化程度比较落后,人们干活大都是用手提肩扛。这不!打房顶的混合泥和好后,房顶上有几个人把绳子系到下面,下面的人将和好的老炕土装进筐子里,再一筐子一筐子提到屋顶上,将泥从房顶的一头一筐一筐挨着倒,等把所有的老炕泥全部运到房顶后,再有技术人员一一摊平。接着,父亲又找来二十多个乡亲,到房顶上用双脚一一将泥土踩实。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约上五六个小伙伴儿,来到我家的房顶上,加入到踩房顶的队伍中。中午一吃过午饭就开始上房踩房顶,直到把房顶踩磁实了,经管事的检验合格后。再用一到两个比较光滑的石磙子,在房顶上来回的碾压数遍。只见父亲拿上一些灰泥,不时地在留有小坑和小孔的地方一一补平,擦光,最后整个房顶犹如镜面一般平展。这样做是为了日后房顶不存水,不渗雨。房顶打完后,我们几个小伙伴便跟着大人们一起喝点酒、吃点菜。然后美美地吃上两碗大锅菜和白面馒头,好好地解了一次馋。最难忘的莫过于1977年秋天,大队村委会批了我家一块宅基地。为了早日盖上房子,我找来村里六个壮劳力,一连打了六垛坯。翌年,刚过完春节我家就开始盖房子。从打地基到垒大墙再到上房顶,都是村里的乡亲们攒忙,人们没有收一分钱,有时连饭都没吃。当新房子盖好上了房顶后的第三天,我就戴着大红花在乡亲们的锣鼓声中光荣参军入伍了。从此,攒忙这种义务劳动便在我的脑海中渐渐淡忘。
光阴弹指,瞬间芳华。随着“打工”一词的出现,村子里的一些“能人”和年轻人纷纷走出农村,来到城市里“淘金”。而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那个曾广泛流行于故乡的帮工形式——攒忙,已经渐行渐远,几乎不复存在。亲戚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人情味也越来越淡漠了。如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有的家庭,偶尔需要朋友攒忙的,也是好酒好菜招待,不仅花费不小,还得欠下一笔人情债。难怪,很多人家宁可出钱请人,也不找朋友攒忙了!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还是人们思想观念的一种巨大改变?我不敢妄加议论,自有人们去评说。我想,尽管社会进步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那曾经熟悉而亲切的攒忙之事,还有那一张张熟悉、亲切的面孔已经成了陈年往事,成为满满的回忆。但那些热闹、温馨、亲切、快乐的场景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风干,我多么希望让“攒忙”这一幕永远定格,让她永远驻留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