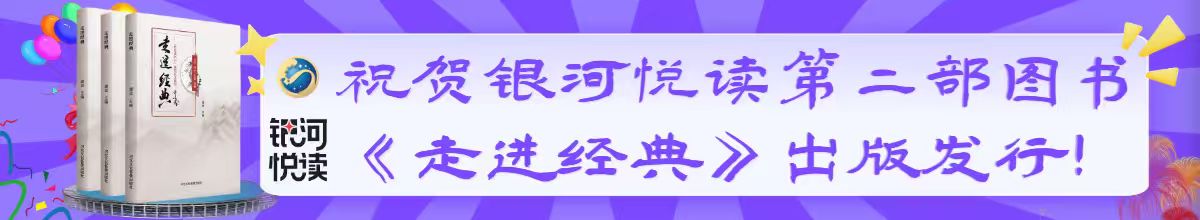从北京乘车,一路向着西北而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群山:燕山—大青山—乌拉山,还有屹立于山巅之上巍峨雄壮的长城。这些山,在我们老家的人看来,都叫北山。在这层峦叠嶂的北山上是一道道高耸入云的山梁,这些山梁,一年三季都是黑色的、灰色的、光秃秃的,只有下了冬雪之后才会变成白色的。我每次回老家时都要坐在靠右边窗户的位置上看这巍峨的山梁,有一次,看着看着,突然发现:这一道道光秃秃的山梁特别像父亲的脊梁,裸露着干硬的骨头架子和青筋暴突的古铜色脊背。越看越像,越像越看,看的我几乎不忍离开眼睛。
一
头一回感觉到父亲的脊梁坚硬,是我五岁那年的春节之后,正月初三那天,父亲送母亲和我们兄弟俩一起去姥姥家拜年,住了一个礼拜后母亲和弟弟留下来了,我和父亲要回家。回家的路是10里山路,父亲拉着我的手,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翻过一座山,又是一道梁,走啊走,走得两条腿疼得厉害,但父亲还是让我自己走。我实在走不动了,很想坐在石头上歇一歇,可是父亲说:“歇什么?男人就要能走路。” “男人就要能走路”,这是父亲给我心灵深处打下的第一个烙印。至今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于是,我咬着牙继续走。走到杨家岭的后山时,刚刚转过山梁,一股白毛风卷着雪粒子扑面而来,打的我转了好几圈才站稳,再向前看去,半山腰里一条崖叉小道已经被厚厚的积雪埋起来了。在这被埋起来的山路上,有一行脚印,每一个脚印都是一个大人也要齐膝的深坑。 我看了害怕得不敢走了,可想起父亲刚才的话,又不敢不走。正在我踟躇不前时,父亲突然一把把我抱起来扔到了他的肩膀上,随后一转,就把我驾在了他的脖子上。 这下可好了,不用自己走路了。我好高兴。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让我骑在他的脖子上。可是,走了没多久,我就感觉到屁股下面被一根很硬的骨头顶的疼。于是,我又要求下来自己走,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继续让我骑着他的脖子走。走啊走,好不容易走过了那一段雪山小路,来到一处避风的阳坡坡,父亲才算把我放下来。然后,摸摸我的小屁股问“还疼吗?”我赶紧说:“不疼了。” 于是,我们又一起朝着家里走去……
二
父亲是个很严厉的人。在他看来,有出息的孩子都是严格管教出来的。所以,要求我们:坐要有个坐相,站要有个站相,吃要有个吃相。对我来说,这“三相”规矩,最难熬的是“坐相”。老家住的是窑洞,三孔窑洞中间一孔为堂屋,东西两侧各一孔为卧室,卧室靠窗户一盘火炕,火炕上面是一领炕席,炕席中间放一张四角饭桌,一家人就盘腿围坐在方桌的四周吃饭。我从小就不会盘腿坐,坐上一会腿就麻了,所以,常悄悄地把一条腿向外伸去,变成了半盘腿坐。为此没少挨骂,有几次,甚至被父亲一脚从炕上踢到了地下,但我还是改不了。好在11岁那年就跑校(走读)到5里外的完小(全称应为“完全小学”,指从一年级至六年级可以完整地在这个学校上完)上五、六年级。每天与父亲聚少离多,挨骂的机会少了,所以,至今没学会盘腿坐。
然而,如果有人欺负我,父亲就会不顾一切地冲上去保护我。在我上小学五、六年级的两年里,虽然每天来回走10里山路,但我的学习成绩,始终是班里的第一名。为此,招来了一些同学的嫉妒。其中有一位比我高一年级(因学习不好降了两次班)的同学,特别不服气。每天放学的路上,他总要找我的茬,要么嫌我走早了没等他,要么嫌我走的快了故意不跟他一起走,有时甚至直言不讳地直接挑衅:“你学习好算老几?打一架试试,我打不扁你不姓W,(他姓W)”,近不得,远不得,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为此,我每天就怕放学。
后来,这事被一位高年级的大姐姐告诉了我的母亲,母亲又说给了父亲。父亲一听就气炸了,直接找到那位欺负我的W同学家,当着他们家的大人放了狠话:“如果你再敢欺负我的儿子,我把你的腿给撇了。”W同学知道我的父亲是个“练家子”(父亲小时候练过武术),而且脾气不好,吓得他再也不敢欺负我了。这才使我顺顺利利地读完了小学五、六年级,考上了中学。
三
记得从小,父亲就教育我们“要争气”,父亲用他自己特有的语言说“不争一口馒头气也要争一口糠窝窝气”。一开始,我们并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懂得父亲是借用“蒸气”与“争气”的谐音用来表达他的意愿。当然,“蒸馒头的气”要比“蒸糠窝窝的气”好闻,但是,只要我们能替他“争一口康窝窝的气”,他就知足了。因而,我们兄妹从小就在学习上没放松过。
记得我考上初中的那年,大队会计拿着一张《入学通知书》走到我家门口对母亲说“你儿子考上秀才了”。 要知道,我在我们这个600多口人的山村里是第四个考上初中的学生。前三个,一个在很远的地方当了老师,第 二个也当了老师,第三个当了空军的伞兵。如果我能考上初中,是父母亲最大的心愿。可是在现场,正当母亲准备接过《入学通知书》的时候,边上站着的一位本家的伯伯却冷言冷语地说:“考上了,考上了还要票子呢!”意思是说,你们家穷的叮当响,还能有钱上中学吗?
二个也当了老师,第三个当了空军的伞兵。如果我能考上初中,是父母亲最大的心愿。可是在现场,正当母亲准备接过《入学通知书》的时候,边上站着的一位本家的伯伯却冷言冷语地说:“考上了,考上了还要票子呢!”意思是说,你们家穷的叮当响,还能有钱上中学吗?
母亲听了这话,没敢吭声,默默地接过《入学通知书》回到了家里,哭了一个下午,她知道,家里确实没有钱。当时,我们家是全村有名的“缺粮户”,也就是村里最穷的人家,因为父亲的身体长年有病,挣的工分少,虽然分的口粮最少,但却仍然是欠生产队的粮款最多的一户。
傍晚,父亲从地里回来了,看到母亲哭红的眼睛,笑笑说:“哭什么,咱家多少辈子没出过一个秀才,现在,儿子考上了,我们说什么也要供他呀。”
过了一会,父亲又对母亲说:“吃饭吧,明天我去借。你放心吧。”
第二天,父亲跟生产队长请了假,肩上搭了一条“毛口袋”出门去了,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可是很晚了还没回来,一连等了两天没回来。那两天,我们娘儿仨个过一会儿就出去看一看,看看父亲回来没有,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等人的焦急心情。
第三天晚上,父亲终于回来了,背回来多半口袋粮食,我们看到父亲背回了粮食,特别高兴,可是打开口袋一看,有玉米,有谷子,还有高梁,都混在了一起。母亲看着这些混在一起的粮食,找来一个大笸箩,又找来一个过滤粮食的筛子,把颗粒最小的谷子筛下去了,把颗粒大的高梁和玉米留下了,然后又一粒一粒地把玉米拣出来,记得那个晚上,母亲几乎就没睡觉,第二天一早,她又端着挑拣出来的谷子上碾子先碾成小米,然后,又把那些玉米也磨成了面。剩下的高梁,父亲又把它背到县城的粮站,换回来15斤粮票。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父亲在那三天中,走过了洋河两岸上百里路的两个县,尤其北山下的那个县,父亲在那里当过短工,于是,父亲就找到他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家去借钱借粮了,无论到了谁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儿子考上中学了,你们借给我点钱和粮,多少都行。秋天新粮下来我就还你们。”结果,三天下来,钱是一分也没借到,粮食嘛,到了谁家都给舀上一升半升的。而且,人家说,“好事啊,不用还了。”可是,人家给的粮食,有玉米,有谷子,还有高梁,父亲出去时,只带了一条口袋,没法分开,只好混在一起背回来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脊梁骨宁折不弯的男人,为了儿子上中学却情愿弯下腰来,象乞讨一样,为我讨来了半口袋粮食。
粮食有了,粮票也有了,钱还没着落呢。父亲给我的二舅写了一封信,当时二舅盲流到内蒙古多伦地区当木匠,比在村里干农活的人们多些收入。很快,二舅就给寄来15元。要知道,在那10个工分仅值2角8分钱的年代,这15元可是大钱了。父亲小心翼翼地穿了两件衣服,把钱揣进内衣口袋里,到县城买回了棉花和布,让母亲给我做了一条棉被和一件三个兜的蓝色学生服,姥姥知道后,又给送来一条新褥子。 我上的那所中学,离家40多里,要住校的。当时,学校规定:可以买饭,也可以用自己带的小米放到伙房去代蒸小米饭。因而,入学那天,母亲给我准备了10斤小米,10斤玉米面做成的炒面和干咸菜,还有15斤粮票,5元现金。父亲用一团花绳,把被褥和衣物给我打了一个背包,背在身上,又把小米、炒面、干咸菜、饭盒放在脸盆里用一个网兜装好了,提在手里,一直把我送到5里外的长途汽车临时站。 一路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当他把我和行李推上那辆当作长途汽车的大卡车上时,他却显得那么吃力。当他正要嘱咐我什么话的时候,司机按了一声喇叭,把父亲吓了一跳,紧接着,汽车就开动了,我坐在卡车的车箱里,看见汽车卷起的尘土中远去的父亲,他正在用手背使劲揉着眼睛,不知道他是被尘土迷了眼,还是真的哭了。
我上的那所中学,离家40多里,要住校的。当时,学校规定:可以买饭,也可以用自己带的小米放到伙房去代蒸小米饭。因而,入学那天,母亲给我准备了10斤小米,10斤玉米面做成的炒面和干咸菜,还有15斤粮票,5元现金。父亲用一团花绳,把被褥和衣物给我打了一个背包,背在身上,又把小米、炒面、干咸菜、饭盒放在脸盆里用一个网兜装好了,提在手里,一直把我送到5里外的长途汽车临时站。 一路上,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可是,当他把我和行李推上那辆当作长途汽车的大卡车上时,他却显得那么吃力。当他正要嘱咐我什么话的时候,司机按了一声喇叭,把父亲吓了一跳,紧接着,汽车就开动了,我坐在卡车的车箱里,看见汽车卷起的尘土中远去的父亲,他正在用手背使劲揉着眼睛,不知道他是被尘土迷了眼,还是真的哭了。
那年,我才13岁,第一次远离家乡去上学,也许父亲是真的不放心啊。
四
三年初中,两年高中,我先后上了5年中学。在初中第三年转学到了离家较近的县城中学,但是,上学的支出一点也没减少。5年中,每月需要4元生活费,每个学期还要5元的书费和学费,入学第二年,学校让村里开了个家庭生活困难的证明,把学费给免了,并且,每学期还给3元助学金,即便这样,光是自己的生活费,每年也要30多元钱才能过下来,这30多元,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怎么办?
每当周末的时候,我就早早回家,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就跟着母亲,带着弟弟,一起上山刨药材,周一早上药材公司一上班,我们就是第一家,卖了药材后还要赶到学校去上第二节课。就这样,还是经常不够用。
这个时候,就显出父亲的重要了。父亲从小就学的一手“挠、剪羊毛”的手艺,每年夏天到来时,就与他的叔叔伯伯和哥哥弟弟们结伴,出去“挠、剪羊毛”。 北方的绵羊,一年能产三茬毛,第一茬是农历五月“挠第一茬羊毛”,这一茬羊毛的羊绒最多,羊毛质量最高;其次是: 农历七月“挠第二茬羊毛”,这一茬的羊绒质量仅次于第一茬;比较差的是第三茬,到深秋时节,天气凉了,还要用剪刀剪最后一茬羊毛,这茬羊毛的土气大,羊毛的“键子(羊毛粘在一起形成的毛疙瘩很难解开)大”,几乎没有绒了。解放前后的几十年中,我们这个家族,每年都能借此挣不少钱,可是,走了集体化之后,再出去干这活儿时,

就只能以生产队的名义,一起出去,挣了的钱,由生产队派人去结算。但是,凡事都有例外。
离我们村二里路的一个小山坳里,有个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姑姑的一家就住在那个村里,那个村里也养着三十多只羊。每年夏天,这三十多只羊的“挠、剪羊毛”就成了父亲的私活儿,每只羊无论是挠,还是剪,只有5分钱,这三十多只羊“挠、剪”一次大概需要两天一夜才能干完。每次挠、剪完后,父亲都能带回来1元5角到1元8角不等的收入。有一年的夏天,我没有生活费了,回到家里等待父亲挣钱回来,可是,整整一个星期天都没等到。没有钱,我就没法去上学。星期一一大早,我就去找父亲,当我来到一座羊圈前面时,老远就听到父亲“吭吭”的咳嗽声。当我走进羊圈里面时,一股恶臭的羊臊味扑鼻而来,呛得我几乎倒退出去,当我捂着鼻子再看时,只见父亲双腿跪在被捆着的一只羊身边,正给那只羊一挠子一挠子地挠着羊毛,而那只羊,不仅不反抗,反而好象很舒服的样子,躺在哪里,闭着眼睛,享受着给它“挠痒痒”。再看父亲,满头大汗,贴身穿的那件母亲给他做的白布坎肩已经被泥水浸泡成灰黄色了。父亲抬眼看看我说:“来了?就剩这一只了,一会就好。” 原来,父亲因为这几天感冒,发烧又咳嗽,所以,手底活儿慢了点,晚了半天。我就站在边上看着父亲边咳嗽边流汗边吃力地挠着羊毛,心头不禁滚过一阵热浪: 我的好父亲,你为了儿子,连身体都顾不上了。
不一会,父亲把最后一只羊的羊毛挠完了,他熟练地把挠下来的羊毛拧成一纽一纽的羊毛卷,然后,收拾行装,把羊毛交给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给了他1元6角钱,父亲1分也没留,转手都给了我。然后,他向生产队长要了一碗开水,拿出两天前母亲给他做的玉米面糢糢,细细地嚼起来。
我怀揣着父亲用不顾自己感冒发烧和咳嗽争来的1元6角钱,离开那个小山坳,向着山外走去,眼前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这条山路通向了山外的远方,目光尽头是北山,北山的山梁上蒸腾着一
团团云雾。云雾之外是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脚下的这条山路通向了去往县城去往学校的方向,我走在这条父亲不知走过多少次的山路上,心潮久久不能平静:这分明是父亲

为儿子铺开的一条走向山外走向远方的路啊,我又一次告诫自己:一定要为父亲争口气!
五
父亲不仅是个种庄稼的好把式,而且在整个农田建设中,也从来不甘落后。
听母亲讲,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刚刚进入高级社时,全公社组织13个村的青年,帮助洋河两岸的几个村子修建引水渠,几百名农村青年集合在一起,挑战担砂子,两个箩筐加在一起,有100斤左右的,也有120、130斤左右的,还有160和170斤左右的。父亲的个子不高,估计不会超过1.55米,但是,他从来都选最重的担子挑,而且,从来都没落在第三名。休息的时候,一大帮年轻人比赛扳手腕,包括一些大个子在内的多数人都败在父亲的手下。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夏天,学校因政治运动而停课了,我回到村里,参加 “三夏”(夏收、夏种、夏锄)的田间管理。我跟着父亲与社员们一起参加了“套地”(用大锄,锄第三遍庄稼)。所有参加“套地”的社员,都是短裤“精牛背”(光背),那天,生产队长没说要竞赛,可一开锄就明显地感觉到大家都峁足了劲要比一比。开锄后,生产队长一路领先,后面的社员们奋起直追,齐腰深的高梁,套地的人们猫下腰去,只见人头晃动,不停地往前蹿。
父亲是最后一个出手的,他看看我:“跟着!”低沉而有力地朝我喊了一句就向前锄起来。
我也跟在父亲的后面,挥开大锄,像模像样地锄起来,锄着锄着进入了庄稼地的深处时才发现,本来每人负责两垅地,而我的另一垅已经被父亲替我锄了,这样就等于父亲锄了3垅,我只锄了一垅,我明白,父亲是怕别人说他的儿子干不了农活,面子上不好看,故意替我锄的。可这样一来,等于父亲一个人要干一个半人的活儿,我的心头一热,加紧了手上的动作,就这样,当一排锄地的社员都到达地头的另一端时,我们也赶上来了。
生产队长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的父 亲,然后诡异地笑笑,说“好小子,跟上来了?”然后,他边掉过头往没锄过的地垅走去,边笑容满面地说“好样的,是郭家的种!”当他走到我的身边后停下来,紧挨着我锄过来的两垅地,调头骑着另外的两垅地往回锄,我们也跟着调头往回锄,没想到当生产队长锄到快中间地段的时候停下来了,他直起腰来,向我招手,让我过去看一看,他指着我锄过地问我“你怎么搞的,怎么两垅地锄的不一样啊,靠你老子的那一垅锄的挺好,靠我这边的这一垅却锄成了这个样子?很多碱草都没锄死,埋起来了”,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
亲,然后诡异地笑笑,说“好小子,跟上来了?”然后,他边掉过头往没锄过的地垅走去,边笑容满面地说“好样的,是郭家的种!”当他走到我的身边后停下来,紧挨着我锄过来的两垅地,调头骑着另外的两垅地往回锄,我们也跟着调头往回锄,没想到当生产队长锄到快中间地段的时候停下来了,他直起腰来,向我招手,让我过去看一看,他指着我锄过地问我“你怎么搞的,怎么两垅地锄的不一样啊,靠你老子的那一垅锄的挺好,靠我这边的这一垅却锄成了这个样子?很多碱草都没锄死,埋起来了”,说到这里他提高了嗓门:
“人哄地皮,地就哄人的肚皮”;
“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
“这个理,你懂啊?”
他的嗓门越说越大,越说越生气,我赶紧点点头。
“回去锄吧!”
生产队长甩下一句,自顾往前锄地去了。
我尴尬地回到刚刚离开的两垅地边,猫下腰继续往前锄,就这样,一直干到正午时分,生产队长才放了话“收工”。可是父亲没收工,他返回去把我锄过的第一垅补锄了一遍才收工。 那一天,父亲不仅没有抢到第一名,而且落到最后一名收工。补锄完工后,父亲把那件灰不灰黑不黑的坎肩往在肩上一搭,招呼我说“走吧!”说完,大步流星地朝着回家的方向走去。 在收工的路上,我跟在父亲的后面,羞愧、难耐的情绪始终笼罩在我的脸上,可是父亲却像没发生什么事的一样,一句也没批评我。我跟在父亲的后面,看着他裸露的后背上,青筋一根根地暴突着,一根干硬的脊梁骨两侧一条条肋骨一凸一凹地显示着它们的不屈不挠。
我的父亲啊,你的儿子不争气,又一次给你抹黑了。
我发誓:一定要当一个顶 天立地的男子汉。
天立地的男子汉。
六
父亲是个有血性的男人。因为他的个子矮,小时候老是受欺负。后来,父亲受人指点,学了点防身术,所以有人说他是“练家子”,但是,到底练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可就因为这
点防身术,受到了村里一茬又一茬年轻人的挑衅,但是,没有一次不是败在父亲的手下。 父亲还是一个不畏强权的人。无论是大队干部还是生产队干部,只要做事不公平,无论是不是他的事,他总要站出来当场揭露人家,甚至当着很多人的面质问人家,弄得这些干部们下不来台。久而久之,父亲成了干部们的眼中钉,一有机会就要压制他,打击他,而父亲则压而不服,越闹矛盾越大,父亲没权,斗不过人家,干生气。时间长了,积劳成疾,浑身上下,全是病。所以,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一个长病人。一年当中,多半年是躺在炕上的。有时候,身体刚刚好一点,他要到街上去散散心,与街坊邻居聊聊天,可是不知为什么,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
我们小时候,只要听到街上有吵闹的声音,多数是父亲与人家吵架或者打架了。所以,后来,我们一听到街上有吵闹的声音,母亲就叫我们赶紧出去看看,是不是父亲又吵架打架了。这样,时间久了,我们兄妹几个一听到街上有吵闹的声音,心就咚咚跳。 当然也有看到父亲英雄形象的时候,有一年秋天,我们放了
秋假,参加生产队收庄稼。那天下午,我们在村东的坡地上收玉米,来了一个当了三年侦察兵刚刚复原的年轻人,也是大队革委会成员之一。他本来按照大队的安排应该在水库工地上搬石头,可是这天不知为什么到生产队来收玉米了。
中间休息时,这个年轻人向父亲叫板,父亲开头 不理他,他就以为父亲怕他了,越来越嚣张,最后竟然诬蔑父亲背后骂大队干部了。他指着父亲的脸说:“我为什么今天回到队里来,就是为了调查你骂大队干部的事。”这下可惹怒了父亲,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想打架?”“打架又怎么的?”年轻人一脸轻蔑地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他的话音还没落,我们也没看清楚父亲怎么动手的,只见那个年轻人连续滚了几个滚,足足滚出去三四米远才停下来。要知道,那年父亲是个快五十岁的小老头,而那个年轻人才23岁,刚刚当侦察兵复原回来,他哪能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于是,他爬起来又朝父亲扑了过去,可是,他刚到父亲跟前,又是几个向后滚,这次滚的更远了。
不理他,他就以为父亲怕他了,越来越嚣张,最后竟然诬蔑父亲背后骂大队干部了。他指着父亲的脸说:“我为什么今天回到队里来,就是为了调查你骂大队干部的事。”这下可惹怒了父亲,站起来问他“是不是想打架?”“打架又怎么的?”年轻人一脸轻蔑地朝着地上吐了一口痰。他的话音还没落,我们也没看清楚父亲怎么动手的,只见那个年轻人连续滚了几个滚,足足滚出去三四米远才停下来。要知道,那年父亲是个快五十岁的小老头,而那个年轻人才23岁,刚刚当侦察兵复原回来,他哪能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于是,他爬起来又朝父亲扑了过去,可是,他刚到父亲跟前,又是几个向后滚,这次滚的更远了。
这个年轻人再起来时,更急眼了,操起一把镰刀就朝父亲冲过去了,这时候,参加收庄稼的人们都上来拉架,有些年龄大的人劝他说:“年轻人,你差的远了,你敢动刀子,他能杀了你,你就忍了吧。” 可是当天晚上,村里的大喇叭响了,要求全体社员都到学校院里去开会。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以为这个会是批斗父亲的大会,正想劝父亲别去了,可是父亲放下饭碗就先去了,我也急急忙忙扒拉了几口饭赶到学校去开会。没想到的是,这天大会的主题是:要求社员们都出勤,秋收交给妇女儿童和老人,青壮劳力都要到水库工地上去,实现 “秋收基建两不误”。
会上,大队书记还点了下午与父亲打架的那位年轻人的名,批评他擅自从水库工地上跑回生产队去,质问他“是不是‘三八、六一队’(妇女儿童的代称)的女人多,吸引了你呀?” 至此,我们才弄清楚,原来他下午回生产队干活,不是象他自己说的那样,回来是调查父亲骂大队干部的事,而是嫌水库工地上搬石头的活太累,擅自跑回生产队来的。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 看到父亲的英雄形象,所以,后来,他再发生打架吵架的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看到父亲的英雄形象,所以,后来,他再发生打架吵架的事,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七
父亲执拗倔强的性格,注定了他是个悲剧型的人物,他的一生就是:一次次挫折,一次次抗争,一次次失败;他不服,再去抗争,甚至到了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地步。他就是这样一个宁折不弯的人,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向强权低头的男人。记得我六岁那年,村里来了1万多民工,都是来帮助我们村修水库的。村里的男劳力就更不用说了,全都上了水库工地,父亲也是天天早出晚归,两不见太阳。冬天到来的时候,西北风呼呼地刮,家里却没有柴禾烧,冷的坐不住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却快要临产了。
那一天晚上,父亲又是很晚才回家,他看见家里实在冷的厉害,就对母亲说“我明儿就上山打一背柴回来,把家烧的暖暖和和的。”母亲疑惑地说:“行吗?肯定不给你请假。人家外村的人都来修水库,你不去行吗?”父亲接着很不在乎地说:“管他呢,干脆我就不去请假了,先打回柴来再说。” 第二天,父亲果真没请假就上了山。因为父亲没带干粮,过了中午我们就等着父亲回来,可是直等到太阳落山了还没回来,母亲坐立不安,带着我和弟弟一起上了窑顶上去等他,风那么大,天那么冷,可是母亲一直站在窑顶上就是不下去,直等到天黑了,才看到东路坡上一座小山似的山柴垛摇摇晃晃地朝着我们家的院子移动过来。到达院门口时因为柴禾太多而一次性进不了院子,父亲就把柴禾放在门外,一抱一抱地往院子里捣,捣了很长时间才算全部捣进了院子里。母亲用笤帚给父亲扫了扫身上的土,让他赶紧进家吃饭。可是,父亲刚刚端起一碗高粱粥来,大队的民兵连长就带着几个民兵进来了,他们催着父亲赶紧去开群众大会,母亲说:“让他吃完饭再去吧。”民兵连长却拦着说“都到了,就等他了”,硬是不让吃。父亲看看不行,放下碗就跟着民兵连长走了。父亲这一走,当晚就没回来,母亲也整整一夜没睡觉。
第二天一打听,才知道,那天晚上,父亲一进会场,就被用绳子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并且,被押到会场的台上去亮相,大队书记宣布了他的罪状:擅自离开水库工地,私自上山打柴,是破坏修水库,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行为。
然后,是公社干部讲话;
再然后,是群众批斗;折腾半夜之后,大队书记又宣布:“押到监狱去!” 父亲一听要把他押到监狱去,朝着大队书记扑通一声跪下去了,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大兄弟,你嫂子就要坐月子了,你把我送走,让她咋活呀?”
父亲一听要把他押到监狱去,朝着大队书记扑通一声跪下去了,低声下气地哀求道:“大兄弟,你嫂子就要坐月子了,你把我送走,让她咋活呀?”
这位大队书记,确实是与父亲没出五辈的本家兄弟,然而,此刻的大队书记却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冷冷地喊道:“带走!”
于是,五六个民兵押着父亲,连夜送到了县城的监狱,而且是步行15里山路送走的。 我可怜的父亲,上山打了一天柴,回到家里连一碗高粱渣子粥都没吃完就被捆了一晚上,批斗了半夜,又连夜送到监狱去了。
当我写到此处时,心如刀绞,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就因为这个事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用我的拙笔把他写出来,写出父亲的男人本性、刚烈血性、敢作敢为、宁折不弯和不得已时委曲求全,以儆后人。 在这个事件中,充分显露出那个年代的农村干部、公社干部的胆大妄为、胡作非为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就因为这个事件,父亲对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再也不相信了,在他的眼里,这些大队干部和公社干部就是一帮无恶不作之徒;从此,他的这位当着大队书记的兄弟就成了他和他的儿子们的心目中的头号公敌。这种仇恨的情绪,在父亲和我们兄弟中先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在我血气方刚的年代曾经设想过若干种替父亲报仇的方法。但却因为条件不成熟没去实施。
这种复仇情绪,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的前一年才渐渐消融下来。
好在中国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在县监狱(也许是看守所,但当地老百姓都叫它监狱)还有懂政策的人。父亲在里边只坐了12天就被放出来了。
出来的那天,一个年龄较大的穿制服讲普通话的干部找父亲谈话,嘱咐父亲:“回家后好好劳动,要去水库工地劳动,不要和大队干部拧着劲”。父亲一一答应了,在他的心里,只要能让他赶快回家,其它都可以答应。
就因为最后这个细节,父亲对共产党始终坚信不疑,他相信共产党是好党,共产党里有好人,临终前还嘱咐我们:“要入党,要相信共产党,要当共产党里的好人。不要当共产党里的坏人。
八
父亲,还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小时候念过三个冬天的私塾,但是,他的毛笔字写的象模象样。每当春节来临时,半个村子的人找父亲写春联,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盘腿坐在方桌前,让我们给他碾墨,他则念念有词地挥笔,一幅幅春联,就从他的笔下流出来了。
父亲还打的一手好算盘,诸如“九九归一”、“狮子滚绣球”(两种乘法和除法运算)等等,他的口诀背的滚瓜烂熟。每当生产队分粮分菜时,会计顾不过来,都要请父亲帮忙。
记得有位大师说过:“越聪明的人越容易得精神病”。还有人说“天才(特别聪明的人)和疯子(精神病患者),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也许父亲就是对他们这些论断的佐证。 由于 父亲的聪明劲儿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但却在农村干部的强权面前一次次地受挫、失败,长期压抑在心头成为积怨,久而久之,造成他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他54岁那年冬天,我回家探亲时,下决心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父亲的聪明劲儿和刚直不阿的性格结合在一起,但却在农村干部的强权面前一次次地受挫、失败,长期压抑在心头成为积怨,久而久之,造成他的精神问题越来越严重。在他54岁那年冬天,我回家探亲时,下决心把他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我们要了一个单间,两张床,我和父亲各睡一张床,我整整陪了父亲22天,每天的工作就是给他喂药喂饭,送屎送尿。房间里有一个炭火炉子,可以烧开水,我每天都把炭火烧的旺旺的,把开水烧的多多的,每天晚上都要给他从头到脚洗一遍,隔一两天给他换洗一次内衣内裤,闲下来时,我就与他聊天,聊他的过去,聊我们家的现在,聊我的弟弟妹妹,聊我的儿子……
父亲说,这是他一辈子最舒心的一段时间。
我们也聊到了那段让他最受辱的蹲监狱的日子,使我怎么也没想到的是,父亲竟然劝我说:“儿子,甭计较他(指那个送他进监狱的书记兄弟)了,把这仇,解了吧。”我瞪大眼睛看着父亲,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他送我参军的路上,还嘱咐我“别忘了给老子报仇”,可是今天,这个处在精神病期间的父亲却一反往常地嘱咐我“忘记那段仇吧,解了吧”。 父亲缓缓地给我解释道:他们家三代单传,可能再过几年他们家就没后(后代)了,这叫天知道,天报应;我们家现在人丁兴旺,你又是军官了,心胸大一点,不要计较他了……
父亲那天说了很多,说的很慢,一句一顿地讲,末了,他还问我:“记住了吗?”我点点头说:“记住了。”他才放心地安详睡去。 我看着沉沉睡去的父亲,眼泪忍不住地流下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农民的心胸!
父亲的病恢复的很快,但我的假期快满了,第23天,弟弟来换我给父亲陪床,我放心地回到了部队。
后来,弟弟来信说父亲基本好了,已经出院了。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转过春节,正月十八这一天,突然接到弟弟发来的电报:“父病故,速回!” 我急急忙忙地请了假,赶到家时,父亲已经入棺了,但还在等我看上最后一眼就要封棺了。
当晚,打开棺盖后,我看到父亲安详地躺着,就象在医院里睡着了一样…… 但是,父亲的身体显得很瘦小,只有肩头的那根干干的骨头还是那么不屈不挠,把一件入殓衣服支的老高,他那坚硬的肩头,曾经扛起家庭的千斤重担,扛起儿子的前程,扛起社会的正义。而今,他已经躺下了,再也扛不住任何东西了,但却化作了山脉,化作了子孙的脊梁,化作了郭家的精神,永远会坚硬地撑在那里……
这就是我的父亲,走完了他55年的人生历程,他走的很安详,走的很自信。
(2016年7月14日写于陕西户县长虹酒店8205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