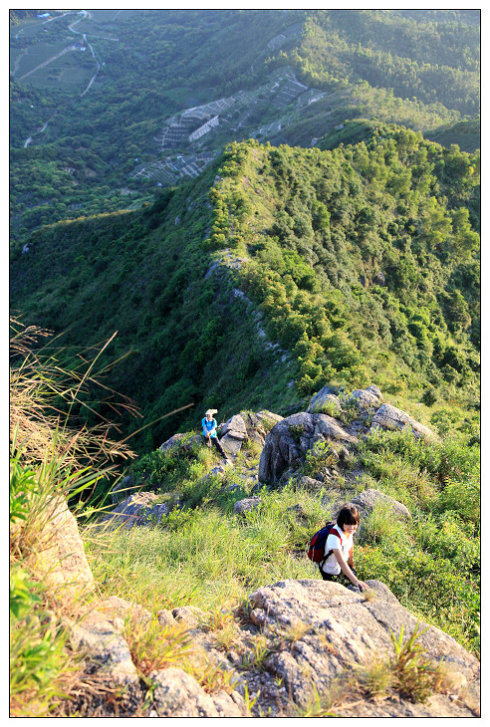
菊花香
牧羊少年的乌毡帽上
东风在寻找去年的好时光。蜿蜒而去的马栏河水
是大地的天空,比一颗盛满爱情的心还纯净
羊群或许接受了山巅的邀请
它们的蹄印留下善良
野菊花开了,开在没有人关注的地方
少年的胸怀很稚嫩
看什么什么都像远去的姐姐
他第一次感受到为别人担心也会流泪
春雨过后,我是新鲜的
春雨过后的原野
看什么什么都新鲜,听什么什么都可爱
阳光在桦树叶上软弱的像一只甲壳虫
几只喜鹊站在枝头
不断地抖动羽毛
落下湿漉漉的夜色,被一朵花抿进嘴里
她要保存好
一定会有人来认领
她在慢慢咀嚼这份不属于自己的幸福
一只饥娥的山羊
小心翼翼绕道而过
而我的心
我突然找到这块丢弃多年的糖
母亲的毛线球在烛光里瘦了
月亮以木偶的方式,在窗上移动
屋里的大黄狗似睡非睡,像一堆忠实的泥土
母亲点燃了蜡烛
她说一来省电二来四十多年习惯了
瞅着烛光心里舒坦
烛光里,母亲的面庞像一幅涂了大红色的油画
曾是无数针尖的划痕
――她两鬓的白发突然生动起来
哦,年轻的白发
还有旧日的苦难,都在她的眼角堆积着
母亲舍不得丢掉
说是一辈子的伴儿
篱笆墙不变
灶台的老式水壶不变
等待春天的火焰,再次沸腾
母亲的毛线球在烛光里瘦了一圈又一圈
仿佛说《春雨过后,我是新鲜的
简单的或最少的就是幸福
桃花与少年
它接受所有的目光
接受被黑夜抛弃的手,东风正在失去茅草屋
从猪圈小路走过来的少年
疯狂生长的黑发,散发初阳的香味
那么迷人。桃花与少年在一起
就是整个世界,在春天里的飞翔
乡村多少事
都在一声春光的吆喝上
亮起前额
少年来到桃树下,朝桃树深深鞠了个躬
然后捧起桃花,匆忙回家
他要用它滋润单亲妈妈失血的嘴唇
离家的车远了
我回头望
那为贫穷而弯曲的炊烟真好看
雨后
一阵春雨过后,原野的颜色重了
在牧羊人的鞭声里,山岗从乳白的纱帐走出
在田地步行的不止是布谷鸟
还有回不去的草鱼
这时候的竹笛
被一个银发老人別在腰间
一只蝴蝶发现:他眼睛有两朵花开了
是他在去蔬菜大棚的田埂上
太阳出来了
村头有人议论说,它是天空下的蛋
刚好被路过的小媳妇听见
她捧着自己身怀六甲的大肚皮
一半是羞涩
一半是骄傲
一辆马车从我身旁的田野驶过
一辆马车从我身旁的田野驶过
它没有停止,也没有对苦菜花说声再见
对泥土的召唤,有不易察觉的颤栗
马车夫不知上哪儿去了
他的泪水还在马眼里汹涌,他的忧郁回到山岗
胡椒林一片美丽如风
我的父亲
总为一个风俗的目光所累
爱人很远,江山很凉
什么也改变不了马车的行进
空空的马车,缺少麦草味和土炕的夜话
如果你肯留下一只草鞋
我就是那只枯瘦的脚
一条小溪到拐弯的时候就不见了
不单是天空
比天空更辽阔的马蹄声看到了
从野妹子岭走下来的一条小溪
它明亮,年轻
它的心轻的像蝴蝶,身体没有留下任何花香
不知道怎么了
到村头拐弯的时候就不见了
年轻时死过一次的人是幸福的
对小溪也是一样
它把芳华献给了故乡
那些红绿的人群,那些湿润的牧歌
那些坚定的有些摇晃的风
属于我最初翻看灶火的一次冲动
一张不易发现的脸
在灰烬里怀素多年
野鸽子飞翔
两座大山的峡谷地带
是红油松的栖息地。我看见多少飞跑的时光
睡眠在这里。野鸽子的飞翔
生动无比,羽毛的坠落都那么自由
没有焦虑的日子
山楂树将心爱的灯光抱得更紧
灯光的源头是一座铁皮屋。里面居住着
两位年轻的逃婚者
他们采集的坚果
胜过自己的文字。那为纯情付出的代价感动一条河流
寂静的日子,就像野鸽子起起落落
他们谁也没说,总觉得少些什么
包括有一天
突然听见敲门声
点燃山峰
没有风,没有故事
夕阳把对面的山峰点燃,最后的耀眼充满惜别
一些金色的马车,在万千归鸟的啼鸣中
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
山羚羊竖起了耳朵
听从山峰燃烧发出的召唤
向受伤的果实靠拢,献出柔弱的心
当河水以铅色跃起的时候
山峰已经是
一块巨大的黑炭。从它裂开的缝隙里
飞奔而来的两匹骏马,坐骑上是父女两个看林人
刚刚点亮的马灯,闪动山峰的味道
灰色夕阳
夕阳终于躲开人群,半卧在地平线上
它不再鲜红。在牧歌中慢慢变紫,变黄,变蓝,变灰
曾经的光芒那么耀眼,穿过伯父的白桦林
就会找到野蜂的家,家是水缸里的月亮
是细如线的炊烟
那为一件红兜肚掀起的风暴
后来被马栏河带走
遥远的东西都是那么值得怀念
我的
在苜蓿地歌唱自由的暮色
你要把我推到哪儿去?我不能接受落日的邀请
这儿有梅花鹿的经血
锄头的反光依然强烈
不停照耀我的手,看见乡亲那么多从前
春雨过后,我是新鲜的
春雨过后的原野
看什么什么都新鲜,听什么什么都可爱
阳光在桦树叶上软弱的像一只甲壳虫
几只喜鹊站在枝头
不断地抖动羽毛
落下湿漉漉的夜色,被一朵花抿进嘴里
她要保存好
一定会有人来认领
她在慢慢咀嚼这份不属于自己的幸福
一只饥娥的山羊
小心翼翼绕道而过
而我的心
我突然找到这块丢弃多年的糖
附点评:
跨越时空界限的现实衔接
——读左岸的组诗《啊,野麦岭》
宫白云
在当代诗人中,左岸是个不可小觑的诗人,什么时候提起,什么时候总有他的一席之地,这是很厉害的,而有的诗人往往昙花一现,他的许多作品之所以像橄榄常嚼常新,与他求新求变不断探索与推陈出新相关。我读过他很多诗歌与随笔评论,“语言”与“个性”这两样东西始终是他的利器。他的语言天分与诗的建构及自由度让他的诗歌诗性总是成色十足。他具有与常人迥然不同的思维与开阔的想象,使他的诗歌意象丰沛,新颖奇特。而且任何事都可以信手拈来入诗,他的组诗《啊,野麦岭》就是如此。《啊,野麦岭》是一部1979年出品的日本老电影,由山本萨夫执导,大竹忍原、田美枝子主演,影片讲述的是在长野县冈谷的缫丝工厂里工作的百余名来自歧阜县穷乡僻壤的“少女军团”的凄惨遭遇。峰、华和菊是其中的代表。她们告别家乡的亲人,翻越野麦岭,踏上了异乡的求生之路。而等待她们的却是超负荷的劳动和工厂主的残酷压榨。峰终因积劳成疾,不幸染上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而被工厂主无情地一脚踢走。她的哥哥星夜兼程,赶到工厂,从破旧的草屋中找到奄奄一息的峰,然而峰却在哥哥背她回家的路上死在野麦岭。诗人选择这部电影为题不仅仅是为了再现这部电影的历史背景,而是为了寄予自己对那些背井离乡者的深切同情与悲悯,因此他才把“我”投入其中,以增强现实之感,来完成他对现实的提醒与折射。
在这组诗中,诗人左岸以他浓郁的笔触,深切的忧伤与高超的语言,顺着“野麦岭”这条主线,以历史的想象力融进自己的视野与思想情感,诗人智慧地把自己隐于其中,让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由历史进入现场。他运用的字眼,句式,看似与电影《啊,野麦岭》毫无关联,但却处处关联,处处隐含。他如一个通灵者走在其中,描摹他的所见所感,凭借内心的悲悯,从“北方”出发,一路风景一路悲欢地通往“野麦岭”历史与现实的深谷,完成他一名观察者与知情者的苦旅,这种隐含苦痛的体验,就像他意味含混的诗写。
佩索阿在他的《不安之书》中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几个人、许多人,都是海量的自我。因此,鄙视他周围环境的那个自我,并不是那个遭受痛苦或者从中取乐的自我。我们自身的存在是一块广阔的殖民地,那上面有着各式各样想法不同、感受相异的人。”而左岸的《啊,野麦岭》正是展示了他许多海量的自我,虽然这组诗是从日本电影《啊,野麦岭》中衍变而来,但“野麦岭”也可看作是诗人“自身存在”的“一块广阔的殖民地”,这块“殖民地”是诗人内心与现实的契约,这个契约不仅承载着诗人的悲悯与同情,同时也是对纷纭复杂的残酷现实生活的一种无声的抗争与揭示。诗人以生命为核心,以时光为手段建筑他自己的“野麦岭”,由此,他看见在“有几个黑蚂蚁大小的人,扛着包裹/匆匆远行,他们没有一个想回过头/看一眼刚变轻的炊烟。其中有一人/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北方》);而“野菊花开了,开在没有人关注的地方/少年的胸怀很稚嫩/看什么什么都像远去的姐姐/他第一次感受到为别人担心也会流泪”(《菊花香》);“离家的车远了/我回头望/那为贫穷而弯曲的炊烟真好看”(《桃花与少年》)。这些诗句仿佛“野麦岭”的一个回声,不断地回到它们的那时,在那里触摸现实的一切。其中“对泥土的召唤,有不易察觉的颤栗”(《一辆马车从我身旁的田野驶过》);而诗人的心也仿佛“突然找到这块丢弃多年的糖”(《春雨过后,我是新鲜的》)。诗人把他一颗尊重生命的情怀放在历史与现实的全景中,从而也就无言地谴责了那些践踏生命者的丑恶。
整组诗看起来都是诗人在自然的呈现,透过那“飞翔”的“野鸽子”;“雨后”的“原野”;“点燃”的“山峰”;“灰色夕阳”,呈现出一种原始生命的质地与深邃,这些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的深切与充沛令人不由得生发许多的感动。贯穿于诗行中的哀伤死亡的气息与回不去的故土情结始终萦绕在读者心头,怎么挥也挥之不去。“空空的马车,缺少麦草味和土炕的夜话/如果你肯留下一只草鞋/我就是那只枯瘦的脚”(《一辆马车从我身旁的田野驶过》);这样的诗语组合除了来自语言自身散发出的魅力外,其实也是诗人借助自然形式来诉说自己对生存命运的深切同情与现实的最终对接。他仿佛也如同“野麦岭”中的那些人无法回到过去,与曾经的“麦草”与“土炕”“夜话”,只能与回味融为一体。当“什么也改变不了马车的行进”时,他只能看着时光的马车从他“身旁的田野驶过”。所以他才说“年轻时死过一次的人是幸福的/对小溪也是一样”(《一条小溪到拐弯的时候就不见了》);所以他才感慨“遥远的东西都是那么值得怀念”(《灰色夕阳》)。另外,这组诗还充满了新奇而独到的比喻,有一首《雨后》最令人难忘:“太阳出来了/村头有人议论说,它是天空下的蛋/刚好被路过的小媳妇听见/她捧着自己身怀六甲的大肚皮/一半是羞涩/一半是骄傲”(《雨后》);把太阳比喻成“天空下的蛋”,也真够胆大妄为的,更出人意料的是画面中竟出现了身怀六甲的小媳妇,“蛋”与“孕”的形象结合,很轻易地就完成了一幅生机勃发的生命蓝图。正因为生命的蓬勃,才更彰显了失去生命的残忍。
诗人借助于电影《啊,野麦岭》来建筑自己的“野麦岭”,很好地完成了生命意义的还原和跨越时空界限的现实对接。
2016-6-10于辽宁丹东跨越时空界限的现实衔接
作者简介:
宫白云,女,当代诗人、诗歌评论家。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流派网副总编辑,《特区文学》读诗栏评荐人,《关东诗人》执行主编,《诗歌风赏》编辑。诗歌、评论、小说等作品散见于各种报刊与选本,获首届金迪诗歌奖年度最佳诗人奖,2013《诗选刊》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5—2016)批评奖。2017年,获得第四届中国当代诗歌奖最佳批评奖。著有诗集《黑白纪》、《晚安,尘世》,评论集《宫白云诗歌评论选》。现居辽宁省丹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