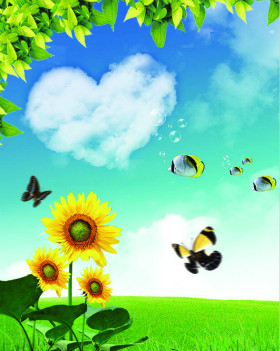
深夜赶写的一篇稿子,横竖不顺眼。在一堆硬邦邦的材料里寻找烟火气,总是费心力。你不想把动人的故事重复成材料,就要不吝啬自己的脚力和眼力,去抵达现场,在你完全陌生的行业里另辟蹊径。这个蹊径,就是你的眼力和心力,灵气和运气。无论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首先应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有烟火气。在写的过程中,能感受到这个人离我不远,甚至很熟悉。那么,我想我应该是写好了。
可这烦人的新冠疫情,困住了眼脚,不能远行,不能抵达。无论我想象力如何丰富,终是赶不上现实的温度。即使我很卖力,依然嗅不到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我总是忽略笔力不足,去诅咒新冠这个害人精。
人哪,习惯了为自己开脱。
修修改改中,又一个上午溜走了。
我想躺下来睡一会儿。
珍珍大娘电话打来时,我在浅睡眠中,来不及一头撞进梦境里。我听见她说,采了一篮子荠菜,鲜嫩鲜嫩。“腾”地我就坐起来了。这个春天的尤物,它长出来了吗?珍珍大娘在电话那头自顾自说着,我听得全全乎乎。大意是眼下该春耕了,庄稼们都等着呢,村庄的出入口已经有序放开,乡亲们走出了家门,开始了春耕。她去田里给金银花剪枝,看见庄稼地里冒出的野荠菜,剪完花枝,采了一篮子鲜荠菜,想让我们尝鲜,吃上第一茬春菜。
也难怪她这么想。
荠菜原本是常见的一种野菜,田野里沟沟坎坎都有生长。少年时在老家,我和小伙伴们挎着篮子去田里挖野菜,挖回的野菜喂猪和鸡。我蹲在院子里剁野菜拌鸡食,时常听见爷爷坐在圈椅上感叹,他说现在的人好过多了,不挖野菜充饥了,都在天顶上活着呢。爷爷心里,吃着窝窝头蒸地瓜,过得就是好日子。不知从哪一年开始,野菜热了起来,逐渐成了餐桌上的“贵族”。价格不菲。人们不遗余力挖掘出它的药用价值、食用价值、养生价值,搬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护生草,性温甘,利肝和中,明目益胃。”不止是荠菜,马齿笕、蒲公英、灰灰菜、牛毛绳等很多被庄稼人称作杂草的野菜,一一走上了餐桌。成了菜品中的好物。人们吃腻了山珍海味,还是怀念旧时的岁月?野菜是红了。
若是爷爷在世,又该作何感叹呢?比天顶更高远的是什么呢?突然很想念爷爷。爷爷若还在,该有多好。
“今年的野菜多,工人们出不来,没人采了。”珍珍大娘的语气里似乎带着遗憾。她口中的工人们,是指邢台煤矿退休的老人。每到春天,荠菜冒出嫩芽,矿上的大爷大妈们三五成群来到乡下踏青,在返青的田野里寻找荠菜。庄稼人从这些“文化人”口中,知道野菜原来这么金贵。但是庄稼人却不认为野菜是好物,尤其老人们。
野菜不管庄稼人和文化人怎么看,由着性子长。
“春儿,能来吗?”珍珍大娘问。
“能。”
对于这位老人,我说不出“不”字。
放下电话,我在日历的空白处写下:“三.八”妇女节,降温,阴天,第一次出县城。
我居住的小区到珍珍大娘的村庄,驱车需要半个多小时。从太行街到西环路,除了交通路口,看到两边大大小小的街巷出口用彩钢板、木板堵着,大约有两米多高。蓝色的彩钢板上贴着告示,再向上是拉起的红条幅,宣传标语写着“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全市动员,全面部署,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戴口罩,勤洗手,科学防守,不串门,不传谣,理性防范”“隔屏不隔心,网上拜年也是团圆”等等口号。各单位门口、小区出口、街道办事处,全部设置了执勤检测点,军绿色、红色、黄色等各种颜色的帐篷格外显眼。出了县城,沿途经过的村庄,每个村口用彩钢板、木棍、土堆等堵着,中间或一侧留着窄窄的通口,电动车可以过,汽车不能出入。村庄路口扯起的宣传标语蛮有意思。例如“老实在家防感染,丈人来了也得撵”“今天到处串门,明天肺炎上门”“不吃野味死不了,不戴口罩阎王找”等等,符合乡村口语。
顺着钢铁路向北,驱车二十分钟,到了珍珍大娘的村庄。进村只有一个路口,彩钢板堵着一半。村民进进出出,胸前挂着蓝色塑料制作的出入证。路口东侧扎着两个军绿色的帐篷,几个值守人员坐在帐篷里聊天,不时探出半个身子向外张望一下,又弯着腰猫回去。丈夫将车子停在大路左边,我从车上下来,向执勤点走去。我看见了珍珍大娘,她坐在三轮车驾驶座上,口罩遮面,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揣进棉衣口袋里。胸前挂的出入证比衣服鲜亮。
我大声喊“大娘”,她看见了我,从三轮车驾驶座下来,在车斗里拿出一个鼓囊囊的袋子递给我:“我寻思城里人稀罕这个,就掐了一些,让孩子们尝尝鲜。”
我双手接过袋子,笑着纠正大娘,县城哪是什么城市,都是村子里走出去的人住在那里,被当作城里人。还不是土生土长的乡娃子。
手中的袋子是温的,在这空旷阴冷的村外,怎么会有温度呢?“我寻思你过来要一阵子,闲着也是闲着,把荠菜择了择,热水锅里走了水,你回去还能省事些。”珍珍大娘语气很平淡。一股热流在我身体里涌动,翻腾。这个“寻思”只有在父母那里才有的浓烈绵长的爱,那是血缘亲情,割不断的牵挂。可是面前这位老人,和我又有着什么渊源呢?
她催促我回去,别杵在这冷天里。我想和她说说话,随便说点啥都行。
没有注意是什么时候,那辆白色丰田车停在马路对面,也不知道车上下来的人是怎么走来的。我看到那个中年男人时,他已站在我们身边,拉住了珍珍大娘的手。那个男人的声音不大,喊了一声“大娘”,珍珍大娘“哦”了一声,背过脸儿打了个喷嚏。俩人向东走了走,似乎要说啥不方便别人知道的事儿。我站在原地没动。只见珍珍大娘一直摇头,使劲摆着右手。那个男人在用手擦脸儿,好像是哭了。又几分钟后,那人“噗通”跪了下去,跪在了珍珍大娘面前,听不清说些什么。
珍珍大娘的身子往后倾了一下。
我想跑过去扶住大娘,又怕自己冒失,犹豫着,不安着。我断定这不是拜年磕头的那一跪。俩人的声音压得很低,隐约能听出话音里的激烈和坚定。而我只能看着,看着一个人跪在冷冽的早春,一个人站在冷冽的早春。
我跺了跺脚,这鬼天气,比冬天还要冷。
但是,谁又能否定它不是春天呢?
丰田车里又下来一个人,是开车的司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那个小伙子走过来,拽起跪在地上的男人。那男人握住珍珍大娘的双手,声音也放大了。我听清了,他说“明天我一定送来!一定!一定啊!”在他“一定啊”声里,小伙子拽着他上了车,开走了。
我跑过去扶住大娘。问她那男人是谁?大娘声音有点抖:“石头跟着他干活儿类。”那个男人说,石头不在了,还有他,他替石头孝敬大娘,明天送三万元生活费。
唉,石头。
我没见过石头,知道珍珍大娘的儿子叫石头。
娘说,石头出事儿后,珍珍大娘哭得没了气。
我安慰娘,人这一生,谁能知道自己会遭逢些啥事呢?如果哭能减轻痛苦,就让她哭吧。
娘是懂珍珍大娘的人。懂她的悲苦和疼痛。她们俩人的缘分,是我善意中犯下的一个错。那是一件很囧的事儿。
四年前的一个夏日,我在娘家小住。骑车去三里外的邢台煤矿菜市场买肉,遇见一对落难夫妻。他们向我伸手,理由是钱被人偷了,没有钱买回家的车票。我没有多想,从兜里掏出五元钱,递给那对落难的夫妻。我想每个在难处的人都应该得到帮助和同情,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相助,也可温暖困境中的人,给与他们生活的信心和希望。“这是骗子,不要给他!”一声严厉的呵斥,让我愣怔一下。循声看过去,一位六七十岁的妇人站在菜摊后面,清瘦的脸庞下,腰板硬挺。她的菜摊上摆着西葫芦、小葱、黄瓜、豆角等时令蔬菜。我看见那对落难的夫妻,狠狠瞪了老妇人一眼。此时,我明白又上当了!爱心用错了对象。我总是这样无原则的去施舍爱,让骗子有机可乘。我觉得那些骗子可怜,骗子大概也觉得我傻吧。那英在《雾里看花》中唱到“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我尴尬地摘下眼镜,揉了揉自己无神的拙目。
那对夫妻卷着我的五元钱理直气壮地离开,消失在另一条街道。
我走到老妇人的菜摊前,挑了两个西葫芦。我问她是怎么判定这对夫妻是骗子?老妇人说:“每天都这几句话,要了很多天。”那你揭穿骗子的伎俩,不怕被报复?她一根直肠不打弯:“年轻力壮不干活儿,净出来骗人,还能成精不成!”老人瘦而不弱,我觉得她很了不起。也为自己的盲目善良感到羞愧。一张车票如何能难住一对中年夫妻?肯吃苦又怎么会挣不到钱?
在娘家小住的那几日,我每天去邢煤菜市场,在老妇人的菜摊前买两个葫芦,或者一把小葱,唠上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儿。
“你们村有个叫闫贵的老头,会看风水,三里五乡的,谁家的孩子成婚都去找他看日子。老头从来不要钱,可厚道了。你年轻,不一定知道,过世好多年了。”
“那是我爷爷。”
“你是他孙女?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你爷爷人好着呢。老头说,和气生财,和睦兴家,日子欢不欢实得看人。哪像现在,合个婚看个庄宅,好吃好喝不算,没个千儿八百的红包不中,好端端的日子都能搅散伙了,一个个都是骗子!你爷爷这样的老头不多喽!”
我“嗯嗯”着。心里想,我爷爷讲得对,人才是最好的风水。日子过得好不好,在人不在命。婚姻不就讲究个和合二字:和气、和睦、合力、合心。
原以为这是朴素的日常,如同每天擦肩而过的路人。
大约是在初秋,娘在电话里告诉我,有个串村卖菜的老人,打听到家里,送了几个西葫芦和一把小葱。娘还说,咱家菜园的菜吃不完哩。
我笑了笑,这老人真有意思。
再后来,爹娘种的北瓜丰收了。送了亲朋和邻居一些,还剩下不少。娘吩咐爹,吃不完的瓜去卖了吧。爹骑着小三轮,拉上五六个北瓜,在邢煤菜市场坐了三天,卖掉两个北瓜,是买一送一。娘数落爹,世上就没见过你这样的笨人,连个瓜都卖不了,瞎耽误工夫。爹冲着娘发火,你去卖吧!整天个没事找事,我卖过瓜吗?每天坚持去蹲点已经不错了,没见过你这样不知足的人!爹和娘叮叮杠杠抬了一顿嘴。娘跟爹赌气,自个在自行车后座捆了一塑料袋北瓜,骑车去了邢煤菜市场,找到送葫芦的老妇人,将北瓜给了她。
娘说,成几个钱算几个钱,卖了算你的,俺不要,不够吃碗热汤面哩。
那我成啥人了?你的就是你的,俺不要。老妇人对娘说。
几天后,乡亲捎给娘十八元五角,是老妇人卖掉的北瓜钱。娘对我们姐妹说,她叫珍妮,以后要喊她珍珍大娘。
石头是在年关出的事儿。
他去要帐,回来路上发生车祸,死了。
石头和正常人不一样,脑子不灵光,有点傻。只知道傻干。结过婚,又离了。石头没有孩子,石头自己就是孩子,他是他娘心里的孩子,也是坏人眼中的孩子。
石头仗义,给谁打工都卖力气。老板说,等等吧石头,等工程款结算了,全部给你算清。每次珍珍大娘问起工钱,石头就说,人家现在不是没钱嘛,等有了就给了。
石头几乎每天出工。他干了多少工,给谁干过活儿,珍珍大娘不清楚。
石头不说。
石头死后,一起打工的乡亲说,石头去找美生要工钱,美生在城里买了楼,住在城里。珍珍大娘从乡亲们口中打听到美生家的住址,找到美生家。美生告诉大娘,石头的工钱都结清了。
珍珍大娘没有纠缠哭闹,也没再找美生要过工钱。她将自己关在家里,不出摊,不卖菜,也不说话。娘说,这样会憋出病来的。隔三差五,娘骑着自行车去几里外的村庄,看望珍珍大娘。
肇事车辆是个破三马,撞人的是个穷人,家中五间老屋住着老少七口人。他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珍珍大娘扔给他一句话,你的命是你娘拿命换的,你给不起。
半年后,珍珍大娘又开始出摊,还是挺着腰板卖菜。买菜的熟人都说,她比以前更瘦了。珍珍大娘在菜市场看见我娘,就往娘的车筐里扔几个葫芦。娘做了水煎包,用食品袋包好,骑车给珍珍大娘送去。
没有人在珍珍大娘面前提起石头,珍珍大娘也不提。
一晃,三年过去了。
我没有想到,美生会下跪;我甚至怀疑,美生喝酒了。
可是,他就那么跪下去了,跪在珍珍大娘面前,跪在春天的路上。
我在想,2020年的一场病菌战,让多少人抖落了心里的灰尘和碎屑,擦亮了浑浊的眼睛活的干净透亮起来。我也相信,随着疫情好转,复工复产有序恢复,人们的生活回到正常,一个新的春天开始了。
站在广阔的田野里,我向着天空、冷风、枯木、脚下的麦田、野草,还有一切正在苏醒和已经出发的生灵,大声喊出:春天,你好!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