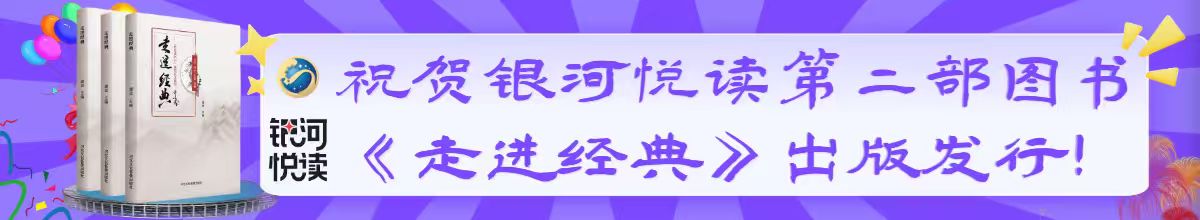我们驻扎在上海及苏州地区一个多月后,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于是,我们就从江苏昆山登上了军列向北启程。
在军列的车厢里,我们度过了几个日日夜夜。睡觉就和衣躺在车厢地板上,用军大衣盖身;吃饭由指定的车站提供,我们下车到月台上蹲着或站着吃。白天行车,我们从车厢门口观看沿途的景象。军列途经苏南、苏北、皖南、皖北、山东、河北,过了山海关,经沈阳、长春,最后进入了吉林境内。白天军列在经过有些地方时,北方籍的战友就会站在车厢门口,默默注视着军列经过他的家乡。有的城市是在夜间不知不觉中经过的。军列在大站停靠的时间较长,以解决官兵的排便问题。
到达通化后,我们还需要在通化农村驻扎一个阶段,要等到来年的一九五三年三月,寒冬过去后,我们再入朝参战。在老百姓家里度严寒有个倚靠。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有火炕作床。炕头烧煤,火舌窜过炕下一条条烟道供热。烘热了炕面,人睡在炕面的被窝里热烘烘的很是舒服。
东北人的家里没有马桶的居多,夜里大小便都要到外面的茅房里去解决。而且屋里的空间小,低矮的房屋结构保暖性很好,但容易变黑发臭,所以,生活条件普遍较差。相信如今那里的生活条件绝对不会再像旧时的样子了。我们在通化驻扎期间,国内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在那段时间里离世。这些政治大事,都由营长曹坤和教导员张步荣集中部队进行了传达。
“白毛呼呼,黄毛呼呼”这是当地人形容冬天情景的民谚。在冬天,东北不仅气候寒冷,而且冬季飘黄沙的日子也多。下雪更是经常有的天气。所以,当地人把鹅毛大雪说成是“白毛呼呼”,另外将飘飞的黄沙形容为黄毛。由于飞来飞去的细微沙尘,漂浮在天空里打旋,遇狂风大作时会发出呼呼的声响,故而有“黄毛呼呼”一说。碰到了这样的恶劣气象日,老百姓一般是不出门的。他们躲在屋里休息,但门缝里、窗框边、依然会有细微的黄沙飘进来,时间稍长,头发上就会蒙上一层黄土。
我们军人要执行野外任务,总不能也躲在屋里。获悉市场上有防风沙的风镜在出售。于是,我们大家都去买了一个回来,作好了入朝作战的准备。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的傍晚,我们在中朝两国的边界河——鸭绿江边的集安火车站登上了军列激情澎湃地越过了鸭绿江铁路大桥。为防止敌机的袭击,火车只能在夜间行驶。这条靠近朝鲜东部山多、隧道多的铁道线,要比朝鲜西海岸的铁路线安全。军列到达了熙川这个军事要地后,我们下车开始了夜行军。这天晚上皎洁的月亮将大地辉映得一片银白,地上的积雪尚未融化,天地之间,被交相辉映的月光和白雪照亮得如同白昼。这是个理想的行军之夜。
我们精神焕发,走起路来劲头十足,未感到疲乏。行军的顺序是,一连最先,营部在后,接着是二连、三连,由机枪连殿后。我走在全连的后面,恰好与营部的领导走在一起。营长和教导员各有一匹战马可骑着行军。但我见张步荣教导员没骑在马上。他和他爱人王佩瑜走在一起。马背上驮着行李物资。我觉得,他这样做很好,有利于树立干部良好作风的形象。
走着走着,我渐渐有了睡意,就边走边打盹,幸亏有月光照路不会跌跤。等到我感觉很累时,天色已渐渐亮了起来,我们的驻足宿营地也差不多到了。部队的先遣人员是提前出发的,他们前去看好住宿的营地,然后分配给随后到达的各单位人员休息。我们在白天休息,晚间行军,这是为了防止敌人的空袭。在朝鲜,志愿军的部队都是这样习惯于昼伏夜行的战斗生活。我们都要每晚赶路,在月光的辉映下,沿途能看到路边歪斜状停着的坦克、战车、以及各种遗弃的装备。可以想见,这里曾经历过激烈的战斗。这些废弃的庞然大物,都是被美军抛弃或是被我军击毁的坦克、装甲车……此时,敌人已败退到三八线以南了,他们驻守在韩国境内继续与我军对峙。
在没有月亮和星光的黑夜行军,行走多有不便。我们自然要全神贯注,额外地消耗精力了。为了避免前后行者的碰撞,大家都把白毛巾扎在背包上,好让后面的战友不吃碰撞之苦。连续多天的夜行军,我们白天得不到安稳的睡觉,疲惫至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才会出现边走边打盹的现象。有时候,就这样走着走着,一下子被路上障碍绊倒了,这才会猛然地惊醒过来。
越是靠近前线的时候,我们还要警惕敌机、敌炮的袭击。我们必须随时作好迅速疏散隐蔽的思想准备。我总算运气好,在朝鲜战场上多次的夜行军中,敌机、敌炮突然的空袭和炮击,一次也没有遇到过。终于,我们顺利到达了第一个预定的驻扎守备的目的地。
三月的朝鲜,大地复苏,万象更新。但气温虽趋回升,仍感到冻手冻脚,气候依然处于乍暖还寒的阶段。
白云山在朝鲜的东海岸,靠近该国的第二大城市——元山,此外,离朝鲜工业城市咸兴也不远。这里的地域是朝鲜国土东西向最狭窄的蜂腰部位,全长也仅有二百余公里。因此,美军在攻不下中朝军队防线的情况下,试图集中兵力,在蜂腰狭窄处实施两边夹击的计划,企图切断我军的补给线,妄想歼灭中朝军队。
我们21军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奉令入朝作战的。我们只有增强兵力,作好充分准备,才能够粉碎敌人的侵略企图。
初上千米以上的高山,山上白雪皑皑,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山地远未解冻。我们要在山顶各处驻守阵地谈何容易呀!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先立足在山麓靠近溪涧的地方搭建帐篷住下,然后上山伐木,就地取材搭建工事。工事的构筑采用了“掘开式”的方法。即在山坡上开挖出三面土坎使之成墙,另一面砍倒山上的树木锯成1.8米长度的圆木并将其排列墙。工事的上方同样用原木截成顶梁木铺排成顶盖,然后盖上油毛毡和树枝,再复盖上厚厚一层泥土。这样就可以挡风遮雨了。
我们将山坡向阳面的大批枯叶收集了起来,并将其铺在工事内的地面上,以此作为我们床铺的区域。在这般艰苦的环境里,我们方才明白,为什么早于三月不能上山的道理。确实,如早于三月上了山,那是难以生存的。所以,一定要等到了阳春三月方可上山才行。这也是我军在通化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原因所在。
我们连住在山下,早晚在山下吃饭。中午由人将食物送到山上简单解决。不久我们构筑的供住宿的简单工事都完成了。于是,按各班一处,分配给部队入住。我们连部的住宿工事,是由抽调来的战士构筑而成的。里面住五六个人,大家用一条狗毛皮褥子作床垫,用油布作帘子挂在门口挡风避雨兼采光。
有了住宿工事后,我们就住在山上不再下山了。大家日夜生活在山顶,开始了昼夜三班轮流打坑道。自此开始,在山顶、山坡、山岗上,到处都可听到“叮当、叮当”的铁镐、铁锤、铁锹的打击声响,昼夜不息。晚上我们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继续工作。所以,当兵的人一定要视力好。近视眼的人,只能做文职工作了。
我没有分配到打坑道的任务。连里要我负责宣传鼓动工作。到各工地去了解、收集好人好事的材料,并写成表扬稿,编成快板节目,让文娱骨干去现场说唱鼓动。有时候,我也会替换战士去抡锤、挖土地干上一阵子,等耗尽了体力就罢手。
在高山顶上,我还看到了古战场的遗迹。那些构筑城墙用过的砖块、碎石散落了一地。据说这是当年薛仁贵带队东征的时候,在当地留下来的遗物。
我站在古战场的废墟上,俯瞰远处的山地,只见一条狭窄的小道蜿蜒曲折到我们驻守的山下。我坚信,如果敌人胆敢来侵犯,我军居高临下地开火,必定能阻敌于此地,让其有来无回。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我们这支队伍虽然名为高射炮兵,但事实上,那时候我们还没装备好高射炮武器。因此,在没有接到这防空武器之前,炮兵就当作工兵来接受战斗任务了。
没有炮,也就没有车辆,没有车辆,当我们转移战线,就只能靠两条腿行军。东海岸的防御工事,经过了我们一个多月的昼夜构筑已全部完成。看来敌人已不敢轻举妄动,不可能贸然来侵袭了。鉴此,我们当然也不必再驻守在白云山头等着敌人来登陆进攻了。敌人不会那么蠢,在我军铜墙铁壁般的高山阵地前,胆敢来硬碰硬撞。他们改为在政治上来进行交易——谈判。于是,我军的方针是边打边谈,打打谈谈,只有等敌人吃了败仗,占不了便宜,才会同意进行停战谈判。
在此期间,我部奉命先向中线开进,等到接近敌占区时,突然又转向东线战场。这或许是我军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来迷惑敌人。使他们误判为我军要增加兵力从中线发起进攻,不知道我军的真实意图,是要从东线发起进攻的。于是,他们就忽视了对东线战场的防御。
我们奔赴的是鱼隐山前线。那里是我方60军刚从敌人手中夺下来的阵地。我们21军是去替换60军的。他们需要到后方去作休整和补充伤亡的兵员。我61师181团开上阵地后,在激烈的战斗中,弹药的消耗量非常大。因此,就得源源不断地加以补充。那时候,在火线上,一人打仗,就必须有十多人在运输线上跟进。
我营首先是当作工兵、步兵来接受任务的。在这次战役中,我们被当作运输兵和182团的官兵一样,每夜从十多里外的二线兵站到火线之间来回穿梭地运输枪弹、炮弹、手榴弹等作战物资登上阵地。这样的任务,干部和战士都一样,必须拼力去完成。七月的气温已很炎热,敌人败退时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一时无人收拾,暴晒在野外已开始腐烂,那臭味混杂在硝烟中阵阵飘来,让人直作呕。
在炎热七月的前线阵地上,我和连部文书刘达有一起,住在王龙序当班长的四班在591高地上的坑道内。老王是个资历很深的老兵,山东人,参加过淮海、渡江战役。他对我很友好。我们挤在闷热、潮湿的坑道内,一起度过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战斗日子。战后,他升任连里的副指导员。我调到营部去做干部教员。
这二十多天的坑道生活叫人难忘。在那些日子里,哪怕是晴天,坑道也会渗出水来,使得地面上积水盈寸。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住在坑道里的八、九个人是怎样生活的呢?我们的办法是,在地面上密排子弹箱当床,在木箱上用枯叶摊平作垫,然后用军毯蒙上;山洞顶就用塑料雨披连接起来挡住水滴,使水流到边缘去。吃饭靠炊事班在山下靠溪边的地方做好后,由各班派人去领取。没有蔬菜就靠罐头黄花菜、干菜猪肉罐头下饭。有时后勤部队还会供应牛肉罐头和鸡蛋粉来改善生活。
白天睡在黑暗的山洞里倒还能入睡。但如遇到敌机来轰炸,就不得安宁了。有一次,一架敌机疯狂地俯冲下来,投下的炸弹落在了我们坑道的边上,让大家受惊不小。幸亏没有投中,不然的话,我们非死则伤。这架敌机实在太猖狂了,它从高山那边飞来,飞得很低,都能看清楚机身上的标志了。不过,刹那间,它就飞远了,因为其速度快,所以投弹的命中率就低。有好几次,由于敌机飞得过低,被我军用高射机枪击落或击伤,都有过好几例。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是我难以忘记的日子。在这天夜里,我亲历了敌我双方的炮声同时都在晚上十时整戛然而止的场景。
朝鲜战争打了两年九个月。我和战友们一起在朝鲜奋斗了五年四个月。而我们入朝后真正参加战斗的时间只有四个多月,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停战后帮助朝鲜人民修复战争创伤、恢复生产经济建设,同时也进行军队的自身建设。
七月二十六日,是我们最后一次上火线。二十七日白天,上级向我们传达了当晚十点整将要停战的重大决定。叫大家不要跃出战壕,就待在山洞内待命。这天入夜后敌我双方的炮击依然如常打响,而且比往常的炮火还要密集。双方炮战的激烈程度已达到了前所未有。这是炮兵部队接到上级命令,必须将所有的炮弹在当夜十点钟之前全部打光不能留下。如打不完的,就必须将全部军火带走,不准遗留在阵地上。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在双方的停战协议上规定的,十点钟之后,双方的军队必须从各自的前沿阵地上撤退,一个人也不能留下。我军向北移到三公里以外,美军向南退至三公里以外。中间空出六公里作为非军事区,由中立国派出代表驻扎监察。果然到了夜间十点整,双方猛力密集的炮声就霎时停止了。
这天夜晚。双方开炮的目标已不在杀敌了。各自都是为了耗尽弹药而已。战斗的参与者都知道战争要结束了,在夜晚十点之前,大家都待在山洞深处的安全位置,谁也不乱跑,只要挺过十点钟,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等规定的时间一到,大家都从山上每一个坑道内欢呼雀跃了出来。整个高地上到处都是热烈的欢呼声。据后来的新闻报道,有些美国兵还徒手走向我们志愿军的阵地,那里有很多人立即伸出友善的手来与刚才还是敌人的人相握。这戏剧性的变化,我不在一线未能看到,但可以很快从新闻报道获悉,这种镜头录下的,与篮球比赛结束时的情景极为相似。
停战以后,在一线的参战人员限期撤出了火线。我们驻扎在二线山洞里的人暂时无任务,因此大家都把被褥、衣服拿出来晒太阳。山洞内实在太潮湿了,住久了绝对会得关节炎。虽说此病不会立即发生,但由于病根已经存在了,就怕日久以后慢慢地生变起来,毕竟任何毛病都是有个潜伏期的。停战后我的健康状况尚好,心情也很好。为了庆祝停战胜利,那一天,我搞了一些子弹,然后提着冲锋枪到了山上瞄准了一块岩石接连扫射了一阵,接着再以前方的一棵枯树为目标打了好几发点射。确实,停战以后,大家的心情都是格外兴奋的。
可是,高兴了几天后,我竟发起了寒热病来。这病的症状是三天两头发冷发热,胃口全无,吃不下东西。说起来也真是奇怪得很,在此前的战斗日子里,我每夜随运输队来回几十里上前线输送枪弹、炮弹,那时的身体棒棒的,能吃苦耐劳。如果那时患了这种病,那我该如何抵挡?幸亏战事停了下来,此时有病我已不担心了。
部队是个大家庭,战友之间虽不是亲人,但却更胜亲人。我生病后,不仅领导关心,战友互助,而且病号还有特别做的病号饭菜吃,有卫生员尽心诊治护理。过了一周光景后,我的病终于药到病除,我恢复了健康。
停战以后,我们在591高地上继续住了一段日子后,就撤离去了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驻扎。那个地方很散落,我们连里的干部也作了调整。指导员沈招才患有胃病去住院治疗了。他的岗位由候进孔来接替。他原是61师侦察队的副指导员。我们早在两年前就认识合作过了。所以,我俩能重逢在朝鲜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