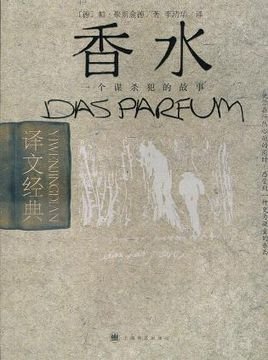
在奥弗涅中央山脉,一个名叫康塔尔山的两千米高的火山山顶上的岩穴里,靠着喝生水、吃野草、蜥蜴、蚂蚁和爬虫,住着一个人。他叫格雷诺耶。
因为敏感非凡的鼻子,他在尘世生活中积攒下十万种气味,然后逃离人群,凭此在荒凉世界盖起一座想象中的气味城堡。白天他幻想在天上飞行,给整个世界播洒各种气味的甘露;晚上他幻想有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味使者给他拿看不见摸不着的气味之书,以及气味饮料和气味美酒,一杯一杯把自己灌醉,最美好的一瓶是被他谋杀的马雷街少女的体香……
这就是《香水》的作者帕特里克·聚斯金德赋予主人公格雷诺耶——这个天才加疯子——看世界的角度。
可是,有一天,他却惊恐地发现: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气味,而他却没有一个“人”应有的味道。这种感觉让他发狂,像踩着烧红的火炭一般乱跳。
他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宫殿”,重新走进人的世界:他要制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香水,他要成为全能的芳香上帝。这种不祥的愿望使他像张着大嘴的狮子,吞噬了一个又一个少女的生命,他把她们的身体变成萎谢的花朵,掠夺了她们的芳香,终于真的制造出上帝一般的味道。
罪行败露,马上要被带到刑场残忍处死的那一刻,他试验了这种香水的魔力——他只不过滴了一滴在身上,在场的一万人,包括被谋杀少女的父亲、母亲、哥哥,就都把他看成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美丽、最迷人和最完美的人。而他像上帝一样面带微笑,谁也不知道他那微微牵起来的嘴角掩饰了什么。
他恨,他嫉妒。这些人卑微,下贱,却拥有尘世的一切。他们有自己的气味,他却没有。他实现了“伟大”的理想,却仍旧是一个无法回到人类世界的幽魂。
臭气熏天的公墓里,格雷诺耶把整瓶香水倒在身上,引诱一群流氓、盗贼、杀人犯、持刀殴斗者、妓女、逃兵、走投无路的年轻人出于绝对和完全的热爱,把自己分而食之。半小时后,这个天才和疯子的合成物,谋杀少女的人犯,伟大的香水制造师,从地面上彻底消失,一根头发也不剩。
《香水》这本小说就像一只大手伸进生活的五脏六腑,好一阵翻搅,从里面挖出最深、最本质的东西:孤独。
因为孤独,他不懂人是要爱人的,也是要被爱的,人的生是值得庆贺的,死却值得悲伤。所有人世一切情意和法则,都被他轻轻忽略掉。他毫不怜悯、毫不手软地害死前后一共二十六个美丽少女,只是为了占有——违背人类通行法则的孤独,就这样成为整个人类的噩梦。
而当他靠着假冒的味道招摇过市,他的“想被认知的迫切感”,也许正是我们共有的焦虑。这里体现的是一个恒久的孤独与追求被认同,但是到最后却命定地永远孤独的命题。
我们生活在群居共食的社会型群体居住环境里,被相同的价值体系支配,认同钱是好的,爱是好的,有朋友是好的,但是,每个人的心里又都有一道幽深的关锁,锁着的,就是那个小小的,叛逆的、孤独的灵魂。所以我们永远不可能像太阳地里那一大片金黄耀眼的向日葵,冲着一个方向微笑,冲着一个方向唱歌,冲着一个方向感恩和祈祷。每一株植物的心里都流淌着孤独的浆液,既渴望被认同,又渴望独立,在反反复复的矛盾中撕裂着自己的灵魂,彼此相望,却不能懂得。
海明威的《战地钟声》里,受重伤的罗伯特打发深爱的姑娘撤离,独自留在阵地,一边竭力在剧痛中保持清醒,一边胡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一句最打动人心:“每个人只能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每个人。”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叫“丧钟为谁而鸣”,其实,对于整个人类世界来说,绝对不必打听孤独的丧钟为谁而鸣——丧钟就为你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