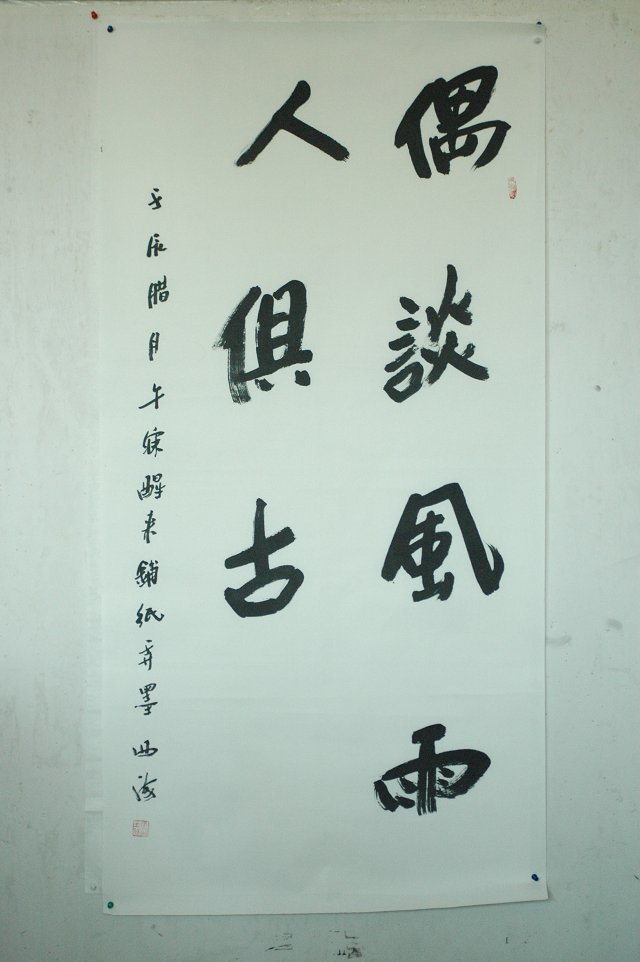
“刘砖头,你木囊啥呢,里面的匠人等米下锅呢!”
砖头的头顶垒着鸡窝。头发一片一片很夸张地竖着,在夏天的太阳地里有些倔强。心里正不舒服,在灰盘前蹲着,手抖抖地摸出纸烟,带把的,主家昨儿个发的,揣在衣兜里,已是邹巴巴的,自己心疼的不行,塞进嘴里,打火机“趴趴”响就是不冒火,本来就燥,不料方向跑出来,扑头就骂,老远飞来的唾沫星很凌厉地打击着他。
刘砖头下意识地躲躲,手里“婆啊婆啊”地挥动铁掀,和开了水泥灰。
因为方向是工头,砖头得靠他吃饭,忍就忍了。
半夜起来,以往工头靠在屋檐下的床空荡荡的,被卷撑成屋顶的形状,桃子的屋里却亮皇皇的。砖头寻了一个避静的角落撒尿,压抑了三十年的青春“刷刷”喷射,还是以往的痛快。按往常,事完后是该唱几句或者吹吹口哨的,因为惦记着桃子,贼一样贴在门框。
……
里面的事情砖头不太明白。他猜方向吃桃子是真的,“啪几啪几”的香。狗日的嘴巴不知道咋弄出的声音,叫人馋的慌,隔着窗子就闻到了香味。
刘砖头因为武功家里穷,得的羊羔疯病,一直没媳妇。
王桃子四十出头,兴平西吴镇人,低个子,喜欢红上衣绿裤子打扮,红辣椒似的性子风格。走路、干活,快,短胳膊碎腿以及手里的家具变魔术一样,浑似刮过黄风让你的眼球做花。父亲老实巴交,丑,言笨,心里有数,身体结实。母亲是四川人,美丽的外表和泼辣的性格,当然还有敢爱敢恨的风流,非一般咸阳本土女人能比。桃子综合了两人的优点,结实,利索,美丽,多情。融入一帮子狼一般男人堆里,便注定发生若干故事。
刘砖头也是男人,也想女人的手。
“婆啊婆啊”,他挥着掀,和水泥叫劲,很想摸桃子的手。一天天过去了,忍着,想着,不小心发现同样两个月没有沾女人的工头方向得手。
有劲没地方使,有气没地方撒,就和门口的沙子干。
“婆啊婆啊”。
月亮下,砖头的脸亮皇皇的,是汗水。
“婆啊婆啊”。
窗户里等亮着,砖头就干。不和灰,就为听个声。
灯灭了。砖头不管,继续。“婆啊婆啊”。
“我问桃子个话,”方向终于披着衣服出来,“砖头兄弟,半夜你干啥活呢,连水泥也不搅?”
“婆啊婆啊。”
砖头不理他,继续忙自己的。方向却钻进自己的“屋顶”,在“婆啊婆啊”里发出火车一样的“忽忽”。
“婆啊婆啊。”
“忽忽忽忽。”
砖头觉得没意思,回去睡了。早上起来,干活没精神,挨了一顿臭骂。
“弄不成,夹铺盖回去,爷另外换人!”方向的串脸胡两个月没刮,土匪似的嚣张。见砖头低头干活,很满意地扭身,又撂下一句。
“臭工头,涨的啥劲,惹急了,爷还不伺候了呢。”砖头偷偷瞄了眼方向的屁股。劳动布面料破了,原来的补丁随着走动在风中“忽闪忽闪”的,象也是骂人。说了只有自己听得见的气话。但心里鼓励自己:“我为啥要走呢,谁规定桃子只能你好?我多挣钱,我也能和你狗日的一样享受呢。”
刘砖头是工队负责活灰的,人称“盘长”。他的工作区域在门外的街道一张铁皮灰盘上,所有的匠人、土工在里面的工地。他一个人天马行空,望着四周的沙子、石子、砖头和水泥,觉得自己是征服世界的强者,自豪的很。
但自从方向从劳务市场叫来做饭的桃子,他有些心不在焉,恨不得把自己的灰盘搬到灶火去。
中午日头端了。刘砖头有些乏,坐在沙子堆抽烟。
“狗日的桃子象这沙子就好了。软软的,还听话。”砖头的屁股体验着生活,沙子被夏天的阳光烘的暖暖的,很体贴地呵护着他被爱情冷落的地方。
“砖头砖头!”桃子叫着跑出来。昨天是红上衣绿裤子,今天却是红连衣裙,在大太阳下裸露着胖胖的胳膊,手腕还带着绿色的冒牌玛瑙玉镯。
“弄啥呢?”砖头心里想和她离近些,最好抱在一起,口气却冷冷的。
“方哥叫你拉砖呢,架板上的匠人等着要呢。”桃子脸上光光的,被灶火的油烟熏的。红嘴唇厚厚的,象砖头后院的火晶柿子。
“你野老汉有命令自己怎么不来,你算哪根葱嘛?”砖头不知道自己的怒火是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喜欢桃子,说出的话却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瓜兄弟,胡说啥呢!”桃子有些羞赧地红了脸蛋,太阳很艺术地装点着她,迷死人了,比电影里哪些白白的狐狸一样的洋女人强出一万倍。
“爷乏啦,不干啦。”砖头索性惬意地躺在松软的沙子里。狠命吸一口纸烟,“嘶——呼”,进去时香香的,吐出来苦苦的,呛的直咳嗽,挣的脊梁骨疼。
“别拧次了,赶紧干活,多挣钱好娶媳妇。”桃子轻轻地拍着他的脊背,呵出的热气弄的他脖项热烘烘的。
“桃子,你这镯子在哪里买的,多少尬?”砖头猛不防抓住桃子的手,问。
“我那口子茂陵会上弄的。”
“戴上凉的很,得是?我听我妈说玉对人皮肤好,很舒服的。”
砖头拉住不放。桃子的手比沙子软多了,而且凉,砖头一辈子头一回感受,自然得抓住机会。
“便宜货,不值钱。”桃子笑着说。近距离,发现男人的下巴疯长的胡须,在逡黑的皮肤土地里洋溢着生机,比自己那个不长胡子的丈夫强多少。喜欢方向,就是因为他串脸胡,而且管着十几个民工还有钱的很。
“我给你买个真的。”刘砖头赌徒劲上来了,手用了力,“桃子,你的手咋这么软这么凉啊?”
“桃子桃子,你在外面弄啥呢!”方向在里面喊。
“我不要。”桃子觉得光棍砖头的可爱,为自己女人的魅力骄傲。听见方向喊,想抽出手。砖头更用力了,她感觉有些疼。做饭的手怎么是捉掀的手的对手。
“砖头!你狗日的不想混了?”背后,刘砖头听见方向已经气呼呼跑出来,才很不情愿地松了手。
“我给桃子看手相呢。”砖头说。
“就是就是。”桃子说着,一路小跑,朝自己工作的灶火跑去。
“看个辣子,里面正砌墙,砖没有了,干锅等着下米呢!”方向一脑子工程进度,外面的事情没心思看清琢磨。看见刘砖头推过架子车,装开了红色的砖头。
“咚咚”,砖夹子把砖堆里的砖放进铁皮车厢。
“咚咚”,刘砖头征服着坚硬的砖头,虎骨上的血管蚯蚓似的,觉得自己的强悍。
“咚咚”,刘砖头想着桃子软软的胖手,假玛瑙镯子,红连衣裙,柿子似的嘴唇,干得有滋有味。
“砖头,这就对了。”方向看他干得起劲,也过来帮忙,说话和和气气的,“咱出门人下苦出力,就图个挣钱过日子。你好好干,哥不亏待你。”
“咚咚咚咚”,刘砖头弯腰只是干。
“桃子,桃子,你做完饭也出来帮忙拉砖!”方向朝里面喊。
“咚咚咚咚咚咚”。
下午上工时,“盘长”刘砖头拆掉了头上的鸡窝,用凉水把头发梳的光光的,中间挑了个缝子,露出白白的头皮,搭眼一看象黑白电影里的汉奸。
“婆啊婆啊”,他继续在四周的沙子、石子、砖头和水泥中间,挥舞着指挥刀一样的铁锨,指挥着自己的千军万马。
手里干活,耳朵伸的老长,扑捉着桃子的音讯。
方向“狗日的”骂个不停,不知道谁又招了祸。以往方向间隙还“桃子桃子”个不停。今个怪了,没有叫。
“婆啊婆啊”。
起初的劲头慢慢绽了。砖头的动作已经是机械运转。好不容易熬到收工,给方向请了事假,出去了。
回来时,已是晚上十点。肚子饿得汩汩叫,爬进去了青蛙,也是顾不上了。
“桃子桃子!”他看见桃子的屋子灯亮着,似乎还有方向的声音。没进去,在外面喊。
“奥。”桃子在里面应,没有出来。
“出来,我跟你说个事么。”
“啥事,你进来说。”
“事情很重要,旁的人知道不好。”
“得啥?”
桃子喜盈盈地飘出门。刚刚洗了头,黝黑的长发城里人一样扎了个马尾,很诱人地斜搭在裸露的肩上。
“你下午干啥去了?”
“你又不是工头,凭什么管我!”
刘砖头原来准备绅士一点,找温馨的话题,谁知道一张口成了质问。桃子也给他来个眼巴朝上。
“我,你。”
“有话快说,方哥正和我说事呢。”
“我,我,我,”砖头把手放进怀里,另一只手抓着了鼓鼓囔囔的蛇皮袋子。
“你吃人呀?”
“给你的……”
刘砖头摸索了半天才笨拙的掏出一把玛瑙手镯,往手里塞。桃子起先以为自己的事他吃醋,会因为自己的冷淡动粗。没想到他这么做。
“我不要,无功不受禄。”
“我化八百元给你到古玩城买的,是正儿八经的非洲货。人家要价两千,我费了好大劲才搬倒了价。”
“我不能要,”刘砖头玩起了心眼,朝屋里奴奴嘴,声音压低,“你得是看上了那货?家里有老婆,和你纯粹是胡整呢。”
“我和方哥是正正经经的乡党关系,你不要胡说。”桃子的声音很大。
“那我不管你了,你把手伸出来,让我给你戴上,行不?”
“我不!”
砖头硬塞,桃子不要。“咣樘”,镯子摔在地上。
“你看你,不怪我奥。”
桃子的脸吓得刷白,直往后躲。她知道,八百元对刘砖头这样的人来说,是下两个月苦才能攒够的,不是小数目。
“不要紧,拾起来让人用胶水一粘还能用。”砖头不恼,弯腰拾起碎成两半的镯子。
桃子没办法,只好接了。她和方向好,是为了让工队免费给自己新盖的房子铺地板砖,可以俭省一千多元。下午掌柜的叫自己回去,只是要了钱,打牌去了。自己有眼泪只能往肚子咽。丈夫是个光顾嘴的男人,啥也干不成,要不,自己一个女人不守在家里,出来和一帮男人混个啥劲。当然,这些话不能给砖头说。
“等一下,还有事呢。”砖头又喊。
“还有啥事?”桃子在心里骂,“方向你狗东西躲在里面装糊涂呢。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这光棍该不是又要耍流氓,欺负我吧?”
“我,你,唉,我不是人。”
“谁说的?你是好人。”
“我,是这,你把这吃货拿上。”
砖头恼怒地煽了自己嘴巴一巴掌,递过来蛇皮袋子。
桃子柔软的胸部被硬硬地碰了。
“啥嘛?”
“我顺路买的桃子。听路上的城市人说,多吃水果美容呢。市场上处理呢,我把他剩下的断堆堆儿全买了。你吃美。”
“砖头兄弟,镯子我要了,我给你钱。这桃子你自己吃吧,你也不容易。”
“你拿上。”
“我不。”
“你拿上!”
“我不。”
“桃子,你在外头弄啥呢,事情还没有说完呢。你要忙,我走了呀。”
里面的方向一喊,桃子趁机跑了。留下砖头抱着蛇皮袋子在原地发呆。
第二天,打圈梁。
刘砖头的活最累。不光是水泥,而且有石子。本来用搅拌机和,方向为省钱,让砖头用人和。自己也过来帮忙。
“婆啊婆啊”。
“婆啊婆啊”。
“婆啊婆啊”。
和自己的情敌干活,刘砖头赌气死了。
“砖头,你得是看上桃子了?”
“婆啊婆啊”。
“你这人,咋不说话?要是看上,哥给她说,她听哥的话。”
“婆啊婆啊”。
“你呀,没出息。”
砖头扔下掀。转身从楼上自己睡觉的地方搬来蛇皮袋子,狠劲一扔。
“我就是没出息,但我是人!”
“谁说你不是人呢?我问你是不是喜欢桃子?”
“我喜欢桃子,咋啦?”刘砖头取出一颗桃子,果子尖尖发软,变质了。他不管,只往嘴里塞,“我吃桃子与你求相干。”
“我不管你,干活。”
“婆啊婆啊”。
砖头和一阵灰,吃一个桃子。
“桃子,出来帮忙。”方向喊。
桃子出来时,砖头已经朝着一大堆桃核吐着唾沫,干得眼红。手里还攥着最后的一只桃子。
“砖头,”桃子喊,用手夺他手里的桃子,“桃子不好克化,再说这桃子放瞎了,不能吃,会吃坏肚子的。”
“你不用管,我就吃!”
“让他吃些。娃娃家,不听大人话,还犟的很。”
“我求你别吃。”
“我就吃!”
桃子想夺,砖头不给。两个人扭成一团,滚了一身水泥。
“干啥呢?这活还干不干?”方向“叭”扔了掀,想制止,拉了这个拉这个,两个犟松谁也不松手。
桃子哭了。
“我不吃了,行不行?”砖头这才扔掉已经在手里变了形的桃子,满手的桃汁,去擦桃子脸上的泪水。
“耍啥流氓呢?”
方向一拳头打在砖头的脸上。
刘砖头忍了。因为,他吃了桃子,还替桃子擦泪水。够了。
“婆啊婆啊”。
“婆啊婆啊”。
“婆啊婆啊”。
终于熬到上楼板,主家高兴,请客。
屁红砖头墙抬起轿子撑起灰色楼板,结婚似的热闹。
艳阳热情挑逗,红色被面子在风中扭摆蛮腰,笑容孩子打滚般在十几张黝黑的脸庞撒欢。房子是在庄基后面建设的,院子前半截空地靠墙,翻斗车很疲惫地趴在地上喘气,十几个匠人每人屁股底下牙着一两块红砖头生硬地发泄着不满,围住两张小方桌,凉的热的,素的浑的,在十几双筷子的点拨中渲染着主人的热情和慷慨。最显眼的是一瓶子绿玻璃包装的“西凤”,灌进塞得满满的口腔。在暧昧阳光和被面的辉映下,一帮子在外盖房的陕西流浪汉们,脸蛋也爬满血液的成色。
“桃子,”匠人堆里的砖头看看喝的正美的工头方向,“哥知道,你的手软的很,凉的很。”
“肉菜塞不住你的臭嘴。别说话,人家不会当你是哑巴。”
“呵呵,大家吃,尽饱吃。”主家殷勤地说。
“吃,喝。”方向也说。
“桃子,你喝酒嘛。”
刘砖头拉了两天肚子,硬撑着,心眼却是最活泛。他的锅底肚皮里蒸熟一堆子万货。腮帮子塞着猪耳朵粉碎,右手执筷子伸向卧在盘子里的鸡,左手却不闲,握着西风朝午餐人群里唯一的女人桃子:“你说你爱我砖头还是方哥?”
“我爱我方哥。”
两寺渡人盖房,有包工和包工包料两种契约方式,匠人们平常自己搭伙吃饭,只是吃饱而已。只有上一层楼板请客,主家掏钱,有菜有肉有酒,过年似的实惠,匠人们放开吃。桃子和工头方向、“盘长”砖头以及其他工友已喝了一大捆啤酒,头晕,脸烧,脑子却清醒,从砖头的口气里听出了醋味,想着自己家的地板砖该铺了,不客气地表白。
“你,我?”
刘砖头摇晃着身子,走到门外的灰盘。
“婆啊婆啊”。又干开了活。
“婆啊婆啊”,他真想多干,而且永远干下去。
刘砖头的头上垒起了鸡窝,头发一片片很夸张地竖着,在夏天的太阳地里有些悲壮。
“砖头,这是你的工钱。”方向把一堆钞票塞进他的手里。掀“啪”地掉在地上。
“还有你的手镯!”
方向扭身回去。里面的人划拳进入高潮。
刘砖头“咚”地一声倒在地上,醉里冒着白沫。他脑子清醒。
“这货病犯了,寻个车送回武功去。”方向对围过来的人群说。
“方哥,我咋不太放心呢,都是可怜人呢。”桃子也喝醉了,在人群里哭哭泣泣地哽咽个不停。
“婆啊婆啊”,在长途车上,刘砖头的脑海里老回荡着这样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