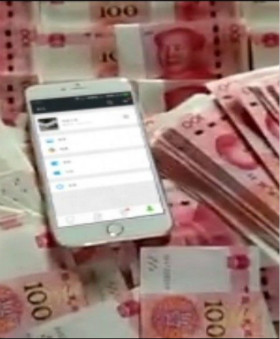
没有任何预兆,一夜间老板被戴上手铐进入看守所。这个消息像一枚炸弹,次日在S公司的办公室里一下子爆炸开来。除了热锅上的蚂蚁或是满屋的无头苍蝇之外,原来的人已不见了。而老板坐进班房的前一周,来自四面八方的旱灾、水灾、地震和台风新闻报道蜂拥而上。瞿佳还没有来得及一声连一声叹气的时候,一个比天灾更厉害“套路贷”的新闻射入她的耳目,瞿佳突然明白老板一夜间人间蒸发的真正原因。
瞿佳站在墙角上,观察着沸腾的蚂蚁和无头苍蝇依然信誓旦旦的模样,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那些灾难的历练催生出智慧的一个个镜头。他们为什么没想到老板突然猝死这么一个假设呢?而非要一意孤行地生出用钱买通各个环节的邪念呢?这样的气势似有一种劫狱的气魄与雄风。然而,麦当劳像稳坐钓鱼船似的,坐在老板上个月从上海艺雕红木家具商场里买回来的红木鸡翅木圈椅上,翘着二郎腿,煞有介事地炫耀,看守所的人他全部搞定。
麦当劳最初的绰号叫肯德基。据说他请人喝茶吃饭全在肯德基里完成而得了这个雅号。可他觉得不好听,听觉上有“啃”的谐音,也给人一种“抠门”的误解。有一次他对所有叫他肯德基的人说,嗨,本人姓麦,你们索性叫我麦当劳吧。于是,麦当劳这个名字便叫开了。当然麦当劳翘着二郎腿坐在这张红木鸡翅木圈椅上,说他全部搞定这件事是在上海老字号饭店里完成的。瞿佳倒抽口冷气,觉得不可思议。虽然说麦当劳的二郎腿很长,但也不可能攀爬到人民检察院的这道门槛。至于别人信与否,瞿佳不得知了。她知道自己站在墙角上观察每个人的心理活动的力度还是有限的。
瞿佳为这件事失眠了几夜。老板这个案子虽然看似与眼前公司经营状况没有关系,但是十年前的房屋买卖的套路贷在今天看来也是一件棘手案子。二十万元钱对于像瞿佳那种每月靠劳动挣一份工资的一介草民来说,万一经受不住这个突如其来的遭遇而无端失踪,确实是一件要命的事。前一阵子她还在数落小姐妹冯甜甜,为什么在一家投资公司理财投资,要等到血本无归的结果才苏醒呢?现在好了,轮到冯甜甜准备来数落她了。瞿佳在失眠的状态里没有与她联系,侥幸地认为自己的遭遇与冯甜甜不可能是一样的。
起床喝咖啡之际,瞿佳没有想到麦当劳会来电话。瞿佳皱了一下眉,但还好没把含在口里的咖啡喷出来。虽然二十四小时的手机畅通,但她也不会想到只是被老板口头封为“副总经理”的麦当劳会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太不懂规矩了!瞿佳很想拒绝,但一想到自己二十万元钱没有解套之前,必须得忍一忍,抬头不见低头见,以致不能让人把话说了。谁知麦当劳一句话让她手中的咖啡杯差点滑下,她真怀疑自己的耳朵已经失聪,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这个当口听到一句“与我合作救老板出来”的话?
听说老板的案子已转移到检察院,你人脉广,想办法赶在马姐前面做好这件事。麦当劳唯恐瞿佳听不明白,反来复去,瞿佳越听越糊涂,马姐与老板是发小,一路风风雨雨都是在互相帮衬中走来,年过大半百,难道这次会出卖老板的利益而自立门户?如果真的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瞿佳觉得麦当劳吃多了肯德基,恨不得要把炸鸡里的骨头带回家熬汤喝,喝得连骨头都能熬化在汤里。法律是为你个人而制定的吗?真是莫名其妙,想入非非,错把肯德基当成麦当劳。瞿佳没好气地把电话挂了。
谁知瞿佳次日一早接到马姐的电话。马姐省去所有的环节,开门见山地朝瞿佳指责道,凭什么说我出卖老板而自立门户?你这样造谣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损人利己也就罢了,损人不利己的事也是像你这样文人做的吗?半夜里喝的咖啡,因处于亢奋状态而一直没有睡着,瞿佳仿佛再次灌进一大杯令人亢奋的咖啡,顺手在身边的玻璃台上重重地拍下,顿时玻璃台面向一边倾斜,差点砸在瞿佳的脚上。她以为自己这样愤怒的动作能让马姐知道她在抗议,然而马姐这些天来似乎被无头苍蝇们飞来飞去已晕头转向,况且麦当劳在她面前陈述是有板有眼的,并且把他打电话给瞿佳的时间也给她过目,在突然失去主心骨的当口上,能有这样的人看护家门并为她通风报信,能不信他而去信瞿佳吗?
瞿佳连忙扶起玻璃台面之际,也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的二十万元钱已不可能轻易追回。风浪四起,船已摇晃,甲板上的人为了逃生互相踩踏,踩痛受伤也必须先上岸,否则什么辩论都毫无意义。瞿佳认为权当自己经历了一次上船前明明听清楚气象台报告今日海洋无风浪,却上船后遭遇风浪袭击。瞿佳想到此,拉黑麦当劳的电话号码后,走到卫生间的洗漱台上,一边打开水龙头搓洗毛巾,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发现遭人当头一棒的结果想象得并不至于那么惨。
然而,当冯甜甜得知这件事后,实在没法理解瞿佳凭什么理由沉默?那天,冯甜甜约瞿佳来到一家S咖啡馆,刚坐下便迫不及待地要弄清这件事。你干嘛要自寻烦恼,人家看到烦恼逃避都来不及呢?瞿佳看着坐在她对面激动万分的冯甜甜,忍不住地反过来劝说一番,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发生?你把麦当劳介绍到公司为老板开车,原本目的是想支开老板的女驾驶员,然而不但没有支开,反而女驾驶员直接睡到老板的红木大床上。对于你介绍进来的麦当劳作为24小时跟随的驾驶员,有良知的话应该劝说老板不能触犯你的底线,可是他做到了吗?当然,老板坐进班房后,那个女驾驶员开着老板为她购买的车子离开了公司。
冯甜甜原本想好好借此机会数落瞿佳一下,想不到服务员还没有把咖啡送上来,就被她轻而易举地揭开了伤疤,伤痛的程度不比她在外投资理财而导致血本无归好多少。能怪谁呢?当初老板让她考驾照做他的司机,可她偏偏握方向盘有一种恐惧感觉,特别是社团里有演出任务,满脑子里都是脚本唱词服饰,老板坐在她驾驶的车上,胆战心惊,发誓不能让她为他开车。后来老板又让她去学会计,结业后能为公司算账管账,但她坐在课堂里,眼睛盯着书本,脑子里却想到社团里那些还没有完成的事,临近考试那几天正好接到社团的通知到外地巡回演出,于是她没多加考虑就拎起背包走人。瞿佳曾直白地说,老板后来被那个杨会计勾引上,一半的责任在于你。演出或展演只是一种爱好,老板为了你的爱好赞助过,但要明白商人是不可能一味地为你付出而不求回报,虽然你们有过夫妻名实。
尽管如此,冯甜甜当得知老板进入看守所,还是让她获得一种从未有过痛快的感觉,她把牙咬得咯咯响,一连说“报应”两字时脑子里闪现出。瞿佳放下手中的匙勺,看了看冯甜甜,冷不防地反问一句,那我在公司里投资的二十万元拿不回来是不是一种报应呢?
这些天来麦当劳坐在老板的红木鸡翅木圈椅上,埋头计算一些筛选的数据。父亲遗留下一个小套房,两位兄长商量下来建议把这一小套给无房的麦当劳,但麦当劳得拿点钱出来给两位兄长作为买下他应得之外的剩余面积。麦当劳曾向老板开过几次口。最后一次老板答应等到他在外收回一个工程的钱之后就给他五十万,然而,正当麦当劳翘首以盼之际,却听到老板被抓了进去的消息。
麦当劳想过老板不出来也就意味拿不到五十万,拿不到老板答应给他的五十万,还有谁能给他这笔钱或者借钱给他?那天夜晚打电话给瞿佳是他觉得这条路只有瞿佳能走得通,谁知瞿佳丝毫不给他面子,他能咽下这口气吗?回想起冯甜甜曾在电话里那一片片责备声,他越发气上心头。在筛选数据之后,他突然感觉到只有和马姐套近乎,只有使出“翻手为云覆手雨”的手段,才有可能尽快解决他自己的事。因此,当他一想到那天向马姐挑起事端,沾沾自喜起来,心想,瞿佳你这个女人,你跟我麦当劳作对有什么好处?
正当这个时候,杨会计穿着一款不合适的旗袍,让一身藏无可藏的肥肉神气活现地出现在麦当劳面前。正在想着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麦当劳,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目光从杨会计一副酒瓶底眼镜片开始一路扫视下去。杨会计警惕性很高,就像对账本上的“借方”与“贷方”每一栏上的数字,时刻与神经的发条拧成一起,大家在背后都叫她“杨神经”。杨会计把报表狠狠地砸在麦当劳面前,一是想让他赶快转移视线,二是为了表示她的气愤,你们胆子也很够大的,模仿老板的笔迹签字,这笔借款究竟去了哪里?
麦当劳的目光正好扫视到杨会计隆起的肉赘小肚上,半晌才站起身,然后走到杨会计的跟前,冷冷地说,你滚圆的屁股擦干净了吗?据所知你经常替老板签字,哪一家公司财务采购一个人的,你平时如何给老板出馊主意只有你自己明白了。现在大家都在献计献策如何及时把老板救出来才是头等大事,你倒好,带着你一身的肉来向我兴师问罪。
杨会计从酒瓶底的镜片里射出两道急促的光,与她喘出急促的气有相一致的节拍。也许刚才的责问声早已传入到隔壁的马姐办公室里,在麦当劳话音刚落下的那一刻,她像影子一样飘到他俩面前,还没有等杨会计反应过来,马姐一把攥住她的胳膊就往她的办公室方向拖。拖到办公室,马姐连忙把门锁上,没好气地责问杨会计,在这个节骨眼上究竟想要干什么?
自从老板坐进班房后,马姐的头发一下子白了一大片。其实心知肚明杨会计究竟要干什么,但她还是要问上一句,仿佛这么一问也给自己喘上一口气。老板倒下势必这个公司完蛋,直到现在她还是坚信老板的初衷并不是像原告的说法“套路贷”,为了这份坚信,她必须从出纳那里拿三十万让麦当劳去铺路。模仿老板签名的是她马姐而不是麦当劳。既然不是麦当劳的责任,干嘛不问青红皂白把矛盾指向他?其他人都可以像无头苍蝇像热锅上的蚂蚁,作为公司的财务总管可以这样感情用事吗?
杨会计好像记起什么来了,一头抱住马姐,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诉说她的委屈。她告诉马姐真有所不知,外人都以为财务与老板总纠缠不清的瓜葛,我每月拿老板的2万元工资是我的价值体现,这有什么可以非议?又说老板为了打通财务上的关节,先诱惑给我钱然后与我同居,这样的流言那个冯甜甜也知道了。冯甜甜现在人既不在公司,也与老板分手了,不是瞿佳告诉她还有谁?她居心何在?老板每月发她工资就是报道与公司无关的内容吗?
马姐耐心地听着,悬在心口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她知道此时头绪都理不清的杨会计已无暇顾及那些被老板的女儿弄丢失的发票和收据了。事实上也是如此,杨会计请求马姐要为她出一口气,她不能容忍瞿佳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马姐爽快地答应她之余,心里也在思忖,打蛇确实要打七寸,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就不信了你这个杨神经不念这份旧情。打发杨会计之后,马姐并没有去找瞿佳问话,前几日经不住麦当劳的挑唆,她觉得自己的含养功夫真是差劲,看瞿佳的气量多大,像没发生过似的,这次真不能莽撞了。要明白目前首当其冲的是想尽一切办法把老板救出来,如果没有“1”的开头,后面再有多少零也没用。
那天晚上马姐依然失眠了。狂风暴雨,还伴有雷击声,上海打破了魔都纪录,连续三次台风正面登录。马姐躺在床上,胆战心惊,唯恐闪电会直接击入她的心脏。她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躲在老板身后,看老板如何打开天井的大门,如何冲向雷雨交加的弄堂,又如何在倾盆大雨里捡回她一只心爱的洋娃娃。她也记得有一年她与老板摆地摊回来的路上遭遇一场雷雨,老板二话没说,拿起摆地摊的塑料纸裹住她与货物,自己淋着雨迎着风,把货物车硬行地推到家里……马姐感受到这次非同以往遇到的灾害。她私下请了一位“生活律师”,希望能从律师的传送纸条中得知老板一点情况,而生活律师所带出来的话只说老板的情绪平稳,人虽然瘦了一点,但精神很好。马姐虽然也让生活律师传话给老板,但心里却是七上八下,照这样下去什么是个头?
就在她准备起来找一片安眠药助睡之际,杨会计的电话闯进来,使她又增加了头痛的程度。杨会计的口吻过于激动,像吃过兴奋剂似的,说起话来连珠炮似的,马姐根本插不进半句话。马姐,你是老板发小,后来并没有成为老板的夫人,但你为啥要把老板的女儿看成自己的女儿,无原则地包庇?
马姐的额头上突然冒出豆大的汗珠,她不明白杨会计究竟要干什么?为了包住女儿不让她受到袭击,老板不是有意让你杨会计即做财务总管,又让你杨会计搞采购了,同时也答应其儿子的每年在国外的学费由老板来承担了吗?我知道老板的好,但老板花心,对人也不公正,那个冯甜甜与女驾驶员……马姐知道杨会计要想表达什么,于是还没有等她说完,没好气地打断她,你明知道老板花心还要与他纠缠一起,我告诉你,你吃那两位醋的人也白白吃,她俩不会同情你……
马姐,你要搞搞清楚,尤其是那个女驾驶员,花了老板多少钱我怎么会不清楚呢?她现在手机号也成空号。杨会计一副神经兮兮歇斯底里的举止,让马姐不知所措。怎么办呢?这样没完没了终于有一天要出事。她不能让这种事态蔓延开来,保护不住老板的女儿,就等于保护不了自己。要知道老板女儿丢失的发票,其中有一部分是为了她。一环扣一环,一旦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时而狂风暴雨,时而热阳高照,瞿佳与冯甜甜顾不上外面天气的一日三变,埋头赶做出国演出服。瞿佳望着自己手中得意的作品,无不骄傲地对冯甜甜说,换一种活法也很幸福。冯甜甜收起最后一根线头,手拿自己的作品走到镜子前,一边试衣,一边接住瞿佳的话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与你这么投缘吗?因为我俩都善于换一种活法来调节自己的心态。我学不会如何掌握方向盘,也看不明白财务上密密麻麻的数据,但我喜欢裁剪缝纫,喜欢舞台,你特地为我量身定做写了一段唱词,我至今唱来也觉得回味无穷。
瞿佳试穿上自己制作的一款青花旗袍大摆裙之后,她开始想象眼前的一枚镜子好比是一个广阔的舞台。镜子里的自己向她展开美丽的微笑,她觉得生活应该这样,人与人之间是相互的,她对冯甜甜说,如果我不进入公司,不可能认识你,如果不认识你,也激发不起深埋在我内心里的东西。尽管如此,两个小女人也不免会谈到投资的钱血本无归的事,谈到血本无归的事,又不免会提及老板和公司近况。
冯甜甜脱下试穿的裙子,重新回到缝纫机前,也顺便拿起电视机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你说,换一种活法也很幸福,然而换的过程并非是一件易事。瞿佳从冯甜甜的眼神里依然看到她对老板不易挥去的一丝情意。她后来才明白冯甜甜从公司里抽去资金向外投资,只是她要发泄的一个桥段,否则怎么才能在转换过程中把握好自己呢?瞿佳觉得自己拿出二十万元投资纯粹是贪小的表现。
电视的几个频道都在播放“套路贷诈骗案”的新闻,冯甜甜触景生情,转弯抹角问瞿佳老板结果会怎么样?瞿佳当然知道冯甜甜充满复杂的心思,但她真无法给她一个好的答案。公司人一开始也这样打探我,现在你也这样问我,可是法律不是为个人制定的,电视新闻你也看得明白,既然是“套路贷诈骗”属于刑事案件,那就不要去幻想他有好结果。想起麦当劳等人的所作所为,瞿佳总觉得老板用人方面有严重的问题。记得有一次她斗大地向老板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被老板数落一顿,说是不是你的小姐妹的意思?这个公司是我的,我知道怎么用人。为了每月工资顺利到达她账户,瞿佳再也没有向老板进言。现在想来这应该是虚荣心将自己“套路”进去。
一连几天雷雨交加,强对流天气影响飞机正常起飞,似乎也影响公司的办公大楼正常秩序。办公大楼走廊上挤满了来要回自己本金的老人,人声鼎沸早已掩过了窗外的雷鸣声和雨滴穿石声。瞿佳跟随冯甜甜在社团里集合,随时听从领导的安排。就在这时,瞿佳接到马姐的电话,马姐的声音不急不慢,让瞿佳反倒生出几分焦虑,索性像上次那样不问青红皂白与她嚷嚷,挂断电话做自己的事也罢了。马姐在向她告知公司今天的情况时,瞿佳的脑海里随时浮现出一种画面。
其实我们都是捆绑一起的蚂蚱,我说明白一点吧,如果公司资不抵债,那么你投资的二十万元也就明摆不可能给你了。马姐一字一句,字字紧扣瞿佳的心。尽管每一句没有提到“老板”二字,但是这个电话的目的让糊涂人也能明白,捆绑在一起的蚂蚱,他们要我做的不就是借我的人脉吗?可是法律不是为个人而制定的,这个信条是她瞿佳始终装在心里而不能轻易去改变的。
我想所有的问题都交给法律吧,我不想再听到我不能解决问题的信息了,瞿佳挂断电话后,独自来到卫生间,站在水龙头前,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沉默无语。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打进来,瞿佳不忍心将他们一个个拉入黑名单。老人们因为信任她才会来找她,此时此刻他们就在公司的大楼里。我们知道你不是公司里的领导,而公司领导就在办公室里,但我们就是信你,你能告诉我们老人投资的钱能要回来吗?瞿佳的眼泪快要掉下来了,一个个苦苦哀求声向她袭来。如果不是万般无奈,有谁会冒着大雨拥挤在闷热的大楼里?我真不知道这个答案,因为我自己也有二十万元在公司里。瞿佳说完就关闭了手机,她感觉再这样下去自己快要疯了。
打开水龙头,将化妆好的整个脸伸进自来水里,感受这种不受任何干扰的刺激,即便冲洗出一个大花脸,也是自己的一块天地。请原谅我吧,我也是一个受害者,谢谢你们这样信任我,但我给不了你们什么,因为我自己也需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关闭水龙头的开关,瞿佳抬头重新将目光正视前方的镜子,一张大花脸呈现在眼前。瞿佳摸了摸自己的脸,然后从抽纸盒里抽出几张巾纸,朝大花脸上抹去,等到几乎抹干净之后,才朝卫生间里出来,而冯甜甜却迎面跑过来,吃惊地叫道,你这是在干嘛?原来躲在卫生间里就是浪费我那高档的化妆品啊。说着,便一把攥住瞿佳的手,一边执意朝化妆间里走,一边还嚷嚷,刚才领导已和我们说了,一个小时后我们从社团出发赴机场。
瞿佳坐下,强作镇静推开冯甜甜手中的化妆品,恳请道,能不能让我素面朝天,等到演出之前再为我化妆。冯甜甜看了看手中的化妆品,停顿片刻,取出一支眉笔,一边为自己补妆,一边向怀揣心思的瞿佳约法三章,我知道你的心思,但我还是想说,谁也不提过去的事,谁提过去就罚酒,直到反胃呕吐酒精中毒为止。
一小时很快过去,从社团出发到机场,一路上瞿佳强打精神与冯甜甜闹笑,谁也不提过去的事,谁提过去就罚酒,直到反胃呕吐酒精中毒为止,她问冯甜甜为什么要打这样狠的赌?冯甜甜说,这样可以逼自己忘记过去,因为生活在继续。
生活在继续,去机场的车也在向前开驶,不一会儿停下,从车的底厢里取出各自的行李,朝机场候机大厅方向走去。正当这个时候,冯甜甜看见眼前的一个小卖部,于是下意识地将手中的行李交给身边的瞿佳,她想到小卖部买两包卫生巾,估计路上要派用场。瞿佳“噗哧”一笑,说冯甜甜青春靓丽,这个年龄还有老朋友与她闹腾。
跨进小卖部门槛,从营业员手中拿到两包卫生巾后,冯甜甜正要掏出手机扫描时,只见身边有个好熟悉的身影,正挽着一个比她年长二十来岁的白头翁,一起把目光朝向货架上的东西。亲爱的,就随便买点零食吧,这里也选不出什么好吃的。白头翁的殷勤让冯甜甜听得毛骨悚然,她想腾出一块地给他们,但已经来不及了,只见对方把脸转过来,将目光朝向冯甜甜。冯甜甜一边扫描支付宝一边倒抽一口冷气,而那个身影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挽着白头翁,嗲声嗲气地要这要那。
瞿佳瞿佳……瞿佳以为冯甜甜遭到失窃了,随她急促的声音,拖着两个行李跑进小卖部。当瞿佳顺着冯甜甜手指的方向,看到那位当过老板的女驾驶员,以及被她挽着白头翁一副亲热的样子,便轻描淡写地说,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嘛,你干嘛大惊小怪?你已经提起过去的事了。
罚酒,直喝到反胃呕吐酒精中毒为止。冯甜甜不好意思地回答。




